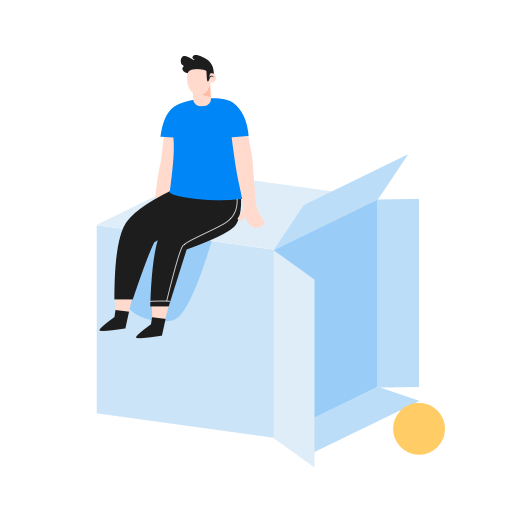康定等(3)
穿过雨雪,靠近阳光,带着诗意的文字纵横川西——新感觉游记系列
一、康定呀拉索
一直觉得情歌中的康定是一匹马、一座山和一朵云的混合体,是张家溜溜的大哥和李家溜溜的大姐放映在天边的一场凡俗的爱情片,打着月亮弯弯的白色字幕。
由于遥远得不着边际,康定对我的诱惑本来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然而,跑马山不会转路却会转,铁路公路、国道省道一直都在转个不停,转着转着就把我们转到了川西。
我们看上去好像是有些被动,但实际上我们是主动的。早在两年前,我们就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在一次摄影展上锁定了康定。这个秋天,我们再度结伴而行,势必要在康定情歌的来处,像亲手抓住一匹马驹一样一把抓住康定。这一回,我们再不会让康定溜溜的城,轻易地从我们的手心和脚底下溜走。
很多年,我一直不觉得康定是一片幅员辽阔的疆域,不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地址,可以用来通信,或是朝里边喊一声就能听到许多亲切的回应。康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抽象了,它既不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也不像是爹妈生出来的,却更像是从嗓子里唱出来的,除了音调和节奏可以把握之外,就再也看不到更多具体的陈设。因此,在我懵懂的青春记忆中,康定简直就像希望一样飘忽而又渺茫。而且,我觉得它一直是侧着身子,背对着阳光在天边吃草。
实际上,真正的康定离天边很远,离成都却不到三百五十公里。真正的康定一点儿也不像情歌那么虚幻。数千年前,它曾经是古牦牛国的核心疆域;数十年前,它曾经是西康省的省会。现在,它仍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当我为了一次旅行,而刻意弄清这些地理概念与历史渊源时,我已经到了不爱唱情歌的年龄。我圆润的青春开始打折,不再是溜溜的大哥。
秋天是一个常常叫人脚板发痒的季节。每到这样的季节,我们都禁不住就会这样想:如果再不出一次远门,如果再不做一次长途跋涉,痒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去康定的理由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天,我们在成都新南门汽车站,买好了下午一点十分去康定的车票。没想到刚刚检票上车,热情好客的成都平原,就已经搭好了广袤的戏台,准备为我们表演一出精彩的川剧。首先登台的当然是新南门汽车站,它一上台就做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变脸动作,不由分说就将发车时间由下午一点十分变成了两点半钟,硬是让我们在臭烘烘的车内苦等了一个多钟头。等到汽车发车驶离成都市区,才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大地也开始跟着变脸了——在新津、蒲江县境内,我们看见四川盆地将屁股一撅,就撅成了丘陵;在丹棱、雅安地界,我们看见丘陵将肩膀一耸,就耸成了高山。车过雅安,318国道接着也表演起了最拿手的堵车绝技,左一堵,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右一堵,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接下来,天空也开始将蓝脸变成了黑脸。随后,车出名山,过天全,穿二郎山隧道,川西高原便在暗夜里进一步绷紧了更黑更黑的脸。黑脸左一甩右一扭的,目的地也就越来越近了。
我们一行六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近十二个小时,才把三百五十公里的距离走完。抵达康定时,无论天空和大地怎么变脸,我们都已经看不清了。直到凌晨两点钟,我们在冷风嗖嗖的康定县城下了车。寂静的街道上灯火阑珊,街道尽头的世界一片漆黑。我们一下车就迷迷糊糊地被一个藏族妇女拉进了宾馆,唯一可以看清楚的,就是她家的宾馆名叫“银华”,宾馆和折多河只隔了一排房子。夜色迷离,寒气逼人,我们还没有和高原见上一面,就已经被它折腾得筋疲力尽。幸好宾馆就在路边,省得我四处寻找,否则,我们真的会被这陌生的夜晚彻底击垮。
关上门,洗掉风尘仆仆,我们就在康定溜溜的城中睡下了。我们听不见自己的鼾声,却能听见折多河水在梦中流得无比欢畅,那汹涌的涛声,简直就是世上最亢奋的一支催眠曲。
那一夜,我们停泊在高原上的睡眠非常短促,大约不足五个钟头。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被一个康巴汉子野狼一样狂野的歌声吵醒了。呀拉索,呀拉索……
我们睁开眼睛,却仍然没有看清康定的摸样。
康定在山上站着,在河边蹲着,在树林中躲着,一直在等我们接近。
那一天,我们在新都桥餐馆里共进晚餐
那一天,我们在四姑娘山四姑拉措旁合影。左起:任哥、何太太、何蔚(楼主)、任太太、曹太太、曹总
那一天,新都桥附近,川藏路旁。藏族司机阿布的家。雨后的天空蓝得发抖。
二、去尼玛的木格措
曙光初现,又一个丰腴的早晨正从跑马山的云缝里露出了臂膀。
我在想,用丰乳肥臀来形容康定的早晨,该不会有很多人投反对票吧?不信,你去看看那些高耸的峰峦和肥硕的草甸,不用解释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撩开窗帘,仰望天空,霞光已经扭扭咧咧地泛起了胭脂红。此时此刻,我们一行人,满怀着疲惫与兴奋,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从折多河水的喧哗声中翻身起床。我们实在是太想早点看到被昨日的夜色藏在被子里的川西高原了。我们实在是太想知道,情歌中的康定,究竟长了怎样的一幅面孔。
我们三个家庭、三对夫妻,出门前就把这次旅行定性为“蜜月之旅”。我们的首选目的地便是康定木格措,然后是新都桥,然后是塔公和八美。如果天气晴好,再然后我们可能还会趁势北上,顺便看一眼道孚的玉科草原和亚拉雪山。
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朝四周张望。简短的街道和低矮的楼房,暂时无法阻挡我们的视线向远方延伸,与天际线实现对接或重叠。实际上,无论我们的视线怎样延伸,也无法逾越那些鼓胀鼓胀的,正在给云朵喂奶的山峰。它们最终只能反射回大脑,成为漫无边际的瞎想。
此时的康定依然是抽象的。唯一不抽象的是,在康定县城,我们与一位私家车主达成了一项非常具体的协议:他同意带我们走“非常路线”,去木格措景区。
所谓“非常路线”,指的就是可以逃票的路线,也是备受驴友背包客们无限爱戴和景仰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的路线,很容易激活沉睡在我们体内的冒险细胞和阶级斗志,很容易让人产生惶惶不安的兴奋感。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逃票经验的菜鸟级驴友而言,“非常路线”更是显得光芒万丈、魅力四射。难怪“逃票”两个字一说出口,立刻就有极少数机会主义分子血压乱窜、躁动不安呢!我们六个人中,至少有一半人可以归纳到“极少数”的范畴。其实这都是被高票价给逼的。凭什么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可以随意卖来卖去,咱们就不能逃他一回票呢?
据我所知,还有一条“平常路线”,是直通着木格措景区大门的,距康定县城只有25公里,来回包车的费用也不过一百块钱左右。木格措景区门票和观光车船票加起来,差不多300来块大洋,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路线完全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像是为官僚资产阶级而专门设定的。逃票,就是对这种不合理路线最有效的否定。
就像康定曾经叫“打箭炉”一样,木格措也曾经叫“野人海”。但不管它叫什么,它现在都已经是中国高原湖泊景区中的明星大腕了,其地位与“艳照门”的主角张柏芝不相上下。我不止一次地在互联网上搜索过木格措,不止一次地在照片上见过这一片由高山海子、原始森林、草原花甸、叠瀑温泉构成的童话景观。木格措景区幅员300多平方公里,仅其中的芳草坪、七色海和杜鹃峡等处个景点,就已经不止一次地让我梦魂萦绕、血脉喷张。
打定了逃票的主意,我们就开始慌慌张张地吃早餐。康定的早餐异常单调,似乎也没有什么特色,一碗牛肉面中找不出两片牛肉,价格却比省会成都还要高。吃完早餐,抹抹嘴巴,我们就上了车。司机(车主)是个40岁左右的康巴汉子,他说,只要我们肯出600块钱租用他的车,他就可以带我们逃票,并且给我们当导游。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最终以400块钱的价格搞定了他。
不幸的是,我们刚一上车,阳光就不见了。我们沿着没有阳光的山路蜿蜒而上,一个小时就到了亚拉神山的某个峡谷口。此时,气温已降至摄氏5度以下,天空忽然飘起了毛毛细雨。司机特意将车停在路边,让我们下车拍照。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几个老外,抢在我们之前占领了有利地形,与我们争起风光来。几个老外在刻有“亚拉神山”标志的石碑前,不停地摆姿势、做表情,我们冒雨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在石碑前留影的机会,于是,我们本能地朝老外翻了几个白眼,就重新回到了车上。
气象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华西秋雨”。这个季节,川西一带一旦下起雨来,没有十天半月是很难停息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我们就杠上了华西秋雨,这确实是一件很要命的事。如果仅仅只是小雨丝丝也就无所谓了,可问题是,就在我们到达红海草原边缘时,雨丝一眨眼就飘成了雪花。待汽车开到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红海草原中心地带时,雪花一抹脸就舞成了鹅毛大雪,气温也下降到了摄氏零度以下。我们在红海草原上喘着粗气,瑟瑟发抖。尽管我们都穿着有内胆的冲锋衣,却仍然抵挡不住突如其来的风雪。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车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红海子朦胧的背影,举着相机却无心拍照。
木格措就这样将我们逐出了它的领地。我们付给藏族司机的导游费也一并打了水漂。
活该!为什么不选一个对的时间和对的路线呢?——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木格措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那就——去尼玛(你妈)的木格措吧!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在心里骂着。
只有天知道,其实我们是在骂自己。
听说新都桥是摄影家的天堂,果然名不虚传。坐在车上,随便往窗外一照,就可以抓到一大堆美景
那一天,在道孚县八美镇街头,阳光当顶照射,艳气逼人。左起:何太太、何蔚(楼主)、曹太太、曹总
那一天,我们三个家庭、三对夫妻,一行六人在四姑娘山脚下合影留念。
看一个个傻头傻脑滴!
上图:雅拉神山
中图:雅拉神山下的溪流
下图:海拔4200米的红海草原(去木格措遭遇大雪)
上图:大雪,红海草原上的心形海子中图:牧场围栏
下图:新都桥途中的草甸 (哦,很抱歉!遭遇大雪,无心拍照,随便弄几张应付应付)
去新都桥的途中,山坡下的藏族民居。随手拍。
三、新都桥,九月的电热毯
新都桥是不是一座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一座海拔三千三百米以上的高原小镇。川藏公路南线和北线在此交汇分岔,像两条张开的布袋口,将康定以西的雪域风光尽收囊中。如果不是一拨又一拨背包客在进藏或入滇的途中遇见了新都桥,如果不是数码相机和互联网替高原上空的飞鸟说出了真相,谁也不会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巴小镇,究竟埋藏有多少美的秘密。
我们是从康定县城直接奔新都桥而来的。那天在木格措,雨和雪左右开弓,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逃窜。当汽车从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红海草原一路滑到半山腰时,我捂着被雨雪扇得发烫的脸对同伴们说了声:还是去新都桥吧!于是,我们就回到了康定溜溜的城,退掉了溜溜的房,重新叫了一辆溜溜的面包车。那一天,一切都是溜溜的,除了心情。
我们沿着川藏公路(318国道)折多山段逶逦而行,一路辗转、盘旋,高处白雪皑皑,低处细雨濛濛。八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耗费了我们四个小时的光阴。到达新都桥时,天依然吊着那张又长又灰的老脸。雨越下越有激情。
我们撑起雨伞,跳下车,在恍若隔世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行走,步子迈得稍快一点,就会让人感到心跳气喘,头晕目眩。我想,若是没有华西秋雨,九月的新都桥本应该是一片灿烂辉煌的光影世界,与天堂的模样不相上下吧?况且,一年四季,川西高原上所有的雪山、草甸、峡谷、河流、湖泊、树林和村庄的静美、秀美、壮美,以及原始之美、自然之美、神秘之美、古朴之美,差不多全都集成在它的身上,无论是一起一伏,一颦一笑,还是一弯一拐,都备受中外驴友和摄影爱好者们的热捧。我甚至是在还没有找到爱它的理由之前,就已经莫名其妙地爱上它了。可是,在雨中,我左顾右盼,却怎么看也看不到一个“新”字——这里的桥是旧的,街道也是旧的。这里的房屋即使是新的,但由于石块筑成的墙壁没有经过粉刷,看上去也依然是旧的。更有趣的是,这里的旧似乎与岁月无关,与历史无关。这里的旧,是无法描述的那种旧,在单纯与简陋之间,在丰富与驳杂之间,交叉重叠着,叫人无法理顺自己的思绪。
所以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神秘本身。要知道,新都桥还有一个相当欧化的名字,叫“东俄罗”,谁也说不清“东俄罗”这个神秘的符合中究竟藏有怎样的况味。
在二郎山外的公路向甘孜境内伸过手来之前,“东俄罗”一直是睡着的,它不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怎么认识它。是川藏公路一把拽醒了它,让它站了起来,动了起来。当川藏公路继而又从汉语词典中将“旅游”这个词带到藏区时,它才猛然醒悟到,原来这个世上不只有牦牛、马匹和羊群的脚印,不只有青稞酒、酥油茶和糌粑的气味,还有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时装、食物、手机和钞票在四处招摇,还有那么多红男绿女在天地间纵情穿梭。从此,寂静闭塞的“东俄罗”改头换面,雪藏了自己的乳名,开始干起了旅游接待的营生。当然,客栈林立的新都桥从此也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失眠症,永远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拥有羊羔一般恬静的深度睡眠。
那天,我在秋雨中仔细地打量着新都桥,试图找到我在图片上见过的某个标志性画面,找到某个似曾相识的镜头,或是与我的想象相吻合的对接点。但是,我在镇子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因此,新都桥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相当模糊的,再加上高原反应从中作梗,就不得不令人产生出许多幻觉,譬如:这是不是一座神经错乱的小镇啊?蓝天是不是放了长假?白云是不是罢了工?到处都是空落落的,湿淋淋的,晕乎乎的,偶尔还有乌鸦从路边的白杨树上扔下几声聒噪,引起我们这些外来人一阵阵耳鸣。这时侯,就连雨声也开始变调,纷纷将清脆的滴答改成了沙哑的颤悠,我们的心情随着雨水的颤悠而继续下沉,很快就沉到了失望的谷底。
天黑前,我们热切期盼这雨哪怕暂停片刻也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街道上,从容地走上一个来回,将新都桥的新与旧看得更加清晰。然而,这么简单的愿望终究还是遭到了雨的回绝。我们仍不死心,执意在雨中转了一圈,谁也不愿意待在宾馆里束手就擒。我们就这样皱着眉头从西走到东,目睹着白杨树和高原柳在雨水中淋浴。目睹着形形色色的藏寨客栈挂着形形色色的招牌,沿川藏公路一字排开,在鲜花和树丛中守株待兔。朦胧中,那些裹着暮气的山峦,依然是草色弥天。山坡上的经幡和六字箴言,依然是庄严肃穆。从镇子中间流过的小河,依然是浑浊而又肤浅。
我们心里很清楚,是雨水打翻了季节的调色板,扰乱了美的秩序,让高原的画布颜面尽失,让仁慈敦厚的天空面目狰狞。不过,雨水毕竟不是常态,雨水背后的晴空才是。晴空之下,新都桥的另一身装束,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如果不尽早出现,那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绕开它,直接去一个没有雨水的城,或是去一座阳光普照的山,与清朗的秋风握手言欢。
但此刻,我们停在了新都桥,我们只能被雨水牵着手东游西荡。泥浆溅到鞋面和裤腿上,冷风呼呼地撞向胸口。转眼间,天就要黑了。我们在镇上找一家干净的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就住进了一家汉族宾馆,准备等到来日,看看天气再决定去留。
九月的新都桥昼夜温差极大,尤其在下雨的夜晚,寒冷和潮湿同时要来敲门,生活中就不得不多出了一些防范。听说,就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已经下过雪了,这时候,所有的宾馆客栈都用起了电热毯。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但仔细一想,若是不用电热毯,你疲惫的身体或许在一夜之间,就会被潮湿的床单读一千遍,直到把你唐诗一样的关节读出风湿来。想想风湿这狗东西虽然很是令人生畏,可这毕竟是在九月啊,出发的时候我还穿着T恤衫,总不至于一嗅到风湿的气味就无条件地向电热毯叩头吧?很抱歉,我做不到。那一夜,我用冰冷的身体挡住了电热毯的诱惑。
冷雨敲窗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天明。半夜里,一群喝了酒的藏族青年跑到宾馆来闹事,他们踢着房门大呼小叫,和汉族老板胡搅蛮缠了很久,才意犹未尽地离去。之后,雨声、耳鸣声和粗野的脚步声开始纠集在一起,剥夺了我们做梦的权利。次日一早,我们去意已决,不管折多山下这座康巴小镇是不是“摄影家的天堂”,是不是户外发烧友的集散地,是不是东俄罗或者新都桥,都已经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马上就要改变行程,向不受雨水困扰的丹巴和小金一线靠拢。
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向北,向东。我们的脚步将在川西版图上划一个巨大的椭圆。
那一天,新都桥至八美的途中,藏族司机带我们去他所在的村庄。
图为搭顺风车去塔公寺拜佛的两位藏族姐妹,她们是新都桥藏族中学的学生,家在理塘。
藏族司机“阿布”家门前的围籬。雨后的雾气在附近的山顶上蒸腾。
这地方很适合逃婚。
那一天,藏族司机“阿布”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子、农具、机械。
阿布的母亲很友善地和我们打招呼,目送我们出村。
四、阳光在撒谎
那天,雨水出乎意料地倒挂在了新都桥上空。千山虚寂,万谷静笃,又一个新鲜的早晨正从川西高原上腾云驾雾而至。我们看见了。
早起的乌鸦在窗外的白桦树上呻吟了很久,还有一些别的什么鸟,也跟着乌鸦一起应和——它们说的是藏文呢还是汉语呢?这悲怆的嘀咕声令人顿生惆怅。我们听见了。
收拾好了行李,吃完早餐,我们准备立刻就弃新都桥而去。就在此时,天空的大脑里突然闪出了放晴的念头。在飘着经幡的山顶和屋顶上,大朵大朵的云不经意间就裂开了一条条缝隙,顿时就有清风朝缝隙中注入了一片片幽蓝。但这一切都留不住我们了。我们相信,比红萝卜还要新鲜的早晨明天还会有的,在丹巴藏寨或日隆藏寨,我们肯定还有机会将同样的早晨从地平线上连根拔起,抛向我们无限敬仰的高空。所以,我们对新都桥没有过多的留恋。我们将搜寻的目光再次转向了新都桥北边的八美和东边的丹巴。
从康定到新都桥,再从新都桥到八美,其间的距离差不多是相等的。散落在山坡和沟谷边的马匹、牦牛和羊群们,它们仿佛占尽了天下的祥和,它们粉红的奶头下吊着漫不经心的原野,日月星辰都像铃铛一样被它们反复摇响。这时,你会想起“岁月静好”之类的有气无力词句,想起无聊的诗歌和神圣的经典。如果此时天空是新的,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只是,在新和旧转换的过程中,说不定你忽然就消失了、遁形了,像露珠一样在人间蒸发。你说不定会脱胎换骨,被另一个自己替代。然后,天的尽头就有了你的飘泊。啊,是这样的——云在云中,雨在雨中,梦在梦中,真实在真实中。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
那天,我们在离开新都桥之前,险些遭到了一群康巴汉子的围攻。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里的藏人根本不和汉人讲什么和谐。在康巴藏区,由于许多地方不通公汽,租车就成了游客们出行的唯一选择。平时,新都桥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中转站,街头常常泊满了形形色色的私车,车主们人多势众,整天坐守街头,虎视眈眈,称雄一方。你只要和其中任何一位车主接洽,都有可能引来一群同伙的参和。如果你势单力薄,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受到威胁、挑衅和敲诈。近几年来,新都桥已经成了许多驴友的伤心之地,没想到我们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凶险,如果不是一位八美的司机帮我们解围,很难预料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那是一段无聊的插曲,颠来倒去地将我们纠缠了很久。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脱身,许多问题都没来得及弄清楚,我们就登上了另一辆去八美的汽车。与我们同时登上汽车的,还有两位腼腆的藏族少女,她们是理塘县人,在新都桥藏族中学就读。她们要搭我们的顺风车去塔公寺拜佛。乌鸦的叫声始终挥之不去。天空呈现出一片片零碎的瓦蓝和羊脂白,云朵和霞光同样挥之不去。
在车上,我听见两位藏族少女管司机叫“阿布”。头发蓬乱的“阿布”挂着两张油黑的刀形脸,他驾驶的五菱面包车正以60码左右的速度,迎面撞向川藏公路北线的一道道风景。公路两旁的青稞刚收割不久,金黄的麦茬为起伏不定的坡地保留了均匀的暖色;沿途的山势如同马背一样平滑而又富有光泽;雨后的河流水位陡涨,波浪覆盖了秋色初染的河床,同时也揉碎了一切事物的倒影。所以,就在黑脸“阿布”带我们绕进村庄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
黑脸“阿布”并不是刻意要带我们去参观他的家,而是因为他的手机忘在了家中。他一点也不在乎这样做是否会耽误我们的时间。黑脸“阿布”的家坐落在平坦的山脚下,两栋石头砌成的小楼,一栋坐北朝南,一栋坐西朝东,一条水泥路直接铺到了大门口,树枝编织的围篱将菜地与水泥路隔开,让传统生活与现代气息互不干扰。树叶刚刚被秋风熏出了黄边的钻天杨,在房前、屋后和路边站得十分随意,一条又清又浅的小溪扭着水蛇腰正要从它们的胯裆下溜走。
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我开始怀疑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事物。我开始怀疑一切的真实。因为那一天,天气预报撒谎了,雨水撒谎了,阳光也撒谎了。天空一会儿蓝一会儿灰,云朵一会儿轻一会儿重,我一会儿聪明一会儿糊涂。我看不见远方,远方被搁置在雪山顶上。我所能看见的近处,山却是魔幻的,拥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炊烟和牛粪;水是魔幻的,拥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清澈和浑浊。那一刻,我怀疑门槛却相信窗子,我怀疑汽车喇叭却相信流水潺潺,我怀疑路途逶迤却相信雾气弥漫,我怀疑树枝摇曳却相信草色匍匐。
因为那一天,眼睛撒谎了,呼吸也撒谎了,唯有饥肠在肚子里说了几句真话。
新都桥到八美的路边,收割后的金色的青稞地,倒映在雨水中的白云后蓝天。这一带,随处都有迷人的景色。
这些片子都是隔着车窗随时拍滴。
如诗如画的村庄,如花似玉的原野,在川藏路两旁静谧着、灿烂着、缤纷着。
不禁会想:若是在这样的村子里找个相好,结果会怎么样呢?
在新都桥一带,你不得不承认,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书写着精彩的童话,每一片天空都吟诵着动人的传说。
那一天,我们的旅程晴过,阴过,雨过,雪过。
那一天,川西高原在不断地为我们变换着丰富的面部表情。
上图:塔公草原,金色的塔尖仿佛与远山的雪线等高
中图:丰收后荒凉的土地,经幡在飘摇
下图:道孚县八美镇乾宁村。送我们去丹巴的司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五、八美是什么美
说起八美,忽然就明白了:美其实是一种常常让人感到饥饿的暗示。正因为有这样的暗示,我们才会加倍喜欢上路的感觉。在路上,美要么是迎面扑来,要么是我们迎面扑向她,那种填不满的饥饿,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饥饿。况且,川西高原上的每一座山都像图钉一样,将美稳稳地钉在地上,风吹不动,水冲不走。况且,在新都桥以北,穿过塔公草原,进入道孚县境内,还有一个名叫“八美”的好地方——呵呵,一个美就足以要人的命了,更何况是八美噢!
新都桥是汉语的新都桥,一说你就能听懂。可八美毕竟是藏语的八美,地地道道的藏语,不是谁都可以听懂的。所以,一路上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在九月,触地即化初雪刚刚涂改了狼毒花的色彩。我不相信一件衬衣,已经裹不住午后的温度。冷开始在神经末梢上停顿下来。
整整四天,我们不停地在路途上奔波,直到可以乌鸦交换歌声,和云朵交换眼神。耳鸣的时候,我更能听见车窗外一闪而过的草原正在哈哈大笑,笑季节的荒诞和牛羊的憨实。而泥土,则依然是一声不吭地想着春天的往事。中度的高原反应,使我不敢相信许多真实的事物,它们总是晃来晃去的,犹如乱花迷人眼。而我在想,再过十天半月,几场雨滋过来,几阵风刷过来,草色就不再绿了,更多的冷空气就有了翻山越岭大动作。我不敢相信到了那个时候,塔公草原的秀发上还能留下几朵情人的插花。我只能说——八美,不管它的脸上有多少条皱纹或是有多少颗青春痘,可它都是八美;不管它的土地有多么瘠薄或是有多么肥胖,可它首饰盒里的金银珠宝,都不会少掉一个数字。
汽车在川藏公路北线噗噗奔驰,草原雪峰历历在目,塔公到了,八美也近了。
按照藏语的说法,塔公意为“菩萨喜欢的地方”。菩萨都喜欢的地方,人当然是更喜欢了。传说塔公曾经是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时走过的路段,山坡上漂浮的云朵中,说不定还游曳着公主沉鱼落雁芳魂呢。川西高原到了塔公这里,海拔高度已经升至3700米以上,黑色柏油路宛如黑色牛皮带一样束紧了大地的腰身,使得塔公草原更加英姿勃发,傲气逼人。这时候,塔公寺金色的塔尖显得格外耀眼,远远地看上去,白雪皑皑的雅拉神山与塔尖之间,仿佛暗藏着一条神秘的等高线。我不想知道究竟是谁刻意制造了这种奇特的视觉效果,我宁愿相信,这是人与神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
在得不到官方媒体关注的前提下,多年来,塔公和八美完全凭着自身的天生丽质,在背包客的长短镜头和日志攻略中悄然鹊起,成为川西高原上最知名的小镇之一。而在此之前,它们不止一次地蒙受神灵点化,所以,你应该相信,草原有耳朵,听得见昆虫唱歌;草原有鼻子,分得清牛和马的汗味,分得清藏人和汉人的体气。我们是汉人,虽然在新都桥熏染了一夜的藏香,可草原依然认出了我们。草原说,拿钱来吧,我让你看个够!马儿说:拿钱来吧,我让你骑个够!可我们还是下意识地捂紧了钱袋,准备抢在下雨之前扬长而去。
我们只在塔公草原边缘停留了十几分钟。看看天,九月中旬的天仍然大面积地阴着,不过天色还早,还不到正午。再看看地,刚刚和夏天分道扬镳的地,上面已经积满了雨水和雪水。最后,我们再看了看苍茫无际的草原,忽然间我们发现,那些被牛羊啃噬和人畜践踏过的草,正在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初雪后的天空亮出了拚命的一绿。
我们知道,那是春天的回光返照。
继续向北。路过土石林,八美正在八里之外等着我们。
没过多久,汽车又像减免债务一样,豪爽地替我们减掉了这最后八里山路。一拉开车门,正午的阳光“嗖”地一声就与我们撞了个满怀,高深莫测的八美也“嗖”地一声站到了我们面前。
一连几天没有见到太阳,到了八美镇,我们一下车就被高原上野性十足的太阳给撞晕了,连眼睛都睁不开。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八美的阳光至少有八两重,那张辉煌的大巴掌一搧过来,我们的脸上立马就留下了一道红印子。
立足未稳,我就开始眯着眼睛朝四周张望,然后,我试着问自己:八美究竟是什么美呢?我一时难以对答。我只能告诫自己,八美只不过是我们去丹巴的一个中转站,据说它曾经是老乾宁县的县城,但对于它,我们的确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我们只是从它的门前路过,只是在它的地盘上转一趟车而已。在我朦胧的印象中,八美仅仅只是一个镇子、一条小街、一座寺庙、一群喇嘛;仅仅只是一场法会、一堆香火、一座村庄、一片树林而已……总而言之,八美不是汉家的公主,不是藏家的外孙,而是川西高原上一道道山梁和一条条沟壑的活体标本,人和牲口,庄稼和草,经幡和云朵,永在其中,来来往往,生生死死,川流不息。
八美不承当任何一种具体的美,它是上苍馈赠给川西高原的一枚橡皮图章,可以为一切看不见的美提供担保,也可以为一切看得见的美签字画押。
甲居藏寨:挂在天边的彩色唐卡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小的县城,它很安静地躺在大渡河谷,四面都是高山,它刻意把自己放了在最谦卑的位置。这个县名叫丹巴,县城名叫章谷。身高:海拔1800米左右。民族:藏。出生年月不详。
在这里,如果你看见阳光给雪山镀金,雪山反过来又给村庄戴上一顶童话的白帽子;如果你看见秋风将青青水果擦红,水果反过来又给门窗挂好了铃铛,你就不会怀疑,丹巴藏寨绝对是中国最美的乡村!
门前挂满了苹果、路边开满了格桑花的村庄,彩虹和霞光的村庄,你走着走着它就会让你飞起来的村庄——
甲居藏寨。云抱着它,雾楼着它,树摇着它,水捧着它……
它是一幅高挂在天边的唐卡。
碉楼在天堂里静谧,经幡在云雾中祈祷。
众人的心愿和众神的箴言,在空气中悄悄传递。
在这里,在这样的时刻,
你走过的路上不会留下脚印,
就像鸟儿飞过的天空不会留下痕迹。
这就是丹巴民居,你可以称它为藏寨或者碉楼。
你来到这里,但这不是你的家。
而当你离去的时侯,你的身体可以带走,
梦却只能永远留在这里了。
寻找你的梦,或许就是你下一次来此故地重游的理由。
高处不胜寒——这是谁说的?其实高处也有暖,既有在暖中茁壮成长的玉米,
更有在暖中无限膨胀的希望。
玉米和希望本来是毫不相干的,
因为你的到来,它们便有了本质的关联。
嗯,这多么好!
啃着亲手从树上摘来的果实,在石头上走一走,在树墩上坐一坐,
在风景中笑一笑,如果还不能满足,那你就真的是贪婪了。
——你要知道,有时候,平民的幸福,也是会让帝王们羡慕的哦!
这一天,我们用偷苹果的手给正在老去的日子抹上了一层釉彩。——想一想,幸福其实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啊!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竟然可以让我们辛苦一辈子,复杂一辈子。
一个傻子问聪明人:永远有多远?聪明人无言以对。
我曾经是那个傻子,但现在,我又成了聪明人。
当村庄、道路和山都来逼问我永远有多远时,我同样是无言以对,只好直接朝它们走过去。
山坡,寂寞的;碉楼,寂寞的;天空,寂寞的;如果一生中,你的心仅仅只拥有一刹那真正的宁静,
那么,整个世界都会是寂寞的寂寞的——就像永远
——就像无数个刹那,为你竖在了那儿。
那么,谁是刹那?谁又是永远?
你的爱人肯定知道。还有这些花朵,它们肯定知道。
花朵在刹那间开放,在永远中凋零。
爱人也是这样的。所以,从今天起,
你必须加倍地珍惜她。必须,加倍地!
此刻,我好奇地凝望着这一座废弃的碉楼,
它什么也没有说,也不知道什么是刹那,什么是永远。
它只是为自己的存在。它很有尊严地站在悬崖边,
让刹那和永远,都找不到冒犯它的借口。
在丹巴,在甲居藏寨,时间变得很有弹性。
在很有弹性的时间里,我们发现:换一个角度看刹那,
刹那是被云雾笼罩的山峰;
换一种心情看永远,永远是被众山挽留的烟云。
来自亚肖神山上的风,不知不觉就能将青青水果擦红、擦黄
卡帕玛雪峰在云中隐隐约约
接下来,是关于米亚罗和四姑娘山的文字,配图是用三洋DV摄像机拍的,画质不太好,但美色不减。
而你读到的文字,将会更优美,更变态——我能保证!!
(更多内容请看我的博客)
日隆镇日隆村,四姑娘山风景区游客中心所在地
▲四川理县米亚罗至马尔康路边风光
天空唯一的一朵云掉进了我的眼底,米亚罗
三千里红叶还没有睡醒,三千里长风
仍在高原之外磨着刀剑。而在此之前
一切活着的事物都快乐着,并且称心如意
▲小金县两河口镇,红军长征时“两河口会议”旧址
翻过鹧鸪山就是马尔康
马背上的阳光很安静地闪亮
牦牛很安静地吃草
古老的小镇很安静地升起了炊烟
历史很安静地躺在纪念馆里,等待着不朽
▲四姑娘山下的日隆镇长坪村
车灯来不及眨一下眼睛
就把一些记忆送到了更远处
陌生的村庄停了下来
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的相机
和我冲锋衣上的灰尘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灰尘
如果我不带来
它们一定还会滞留在别的地方
▲在长坪沟口抓拍到的藏族小妹妹
别的地方哪有这么清纯的一棵火苗啊
自顾自地胆小,自顾自地天真
自顾自地走入没有边际的满足与寂寞
她此刻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复杂和冰冷
就自顾自地简单起来,热起来,美起来
▲黄昏时分,几匹马在长坪沟口准备过河
不知名的溪流和不知名的马儿
一样没有哀愁
雪山有一部分情感在融化
另一部分仍在结冰
融化是幸福的,结冰也是幸福的
每一种幸福都有自己的理由
如同每一种哀伤,都有自己的长短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色的牦牛,以前只见过黑色的
青藏高原是慈祥的
她哺乳着羚羊,马匹,还有牦牛
而牦牛总是喜欢用反哺的方式
将肥美的大地吊在乳头上,摇摇荡荡
像心跳一样大音稀声
像梦想一样大象稀形
▲四姑娘山有60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这只是其中之一
雪山不知疲倦地抱守着一方神秘,这怎么可以
红杉和冷松怎么可以不打招呼就把秋天
领回家中。云怎么可以不站队,就涌进峡谷
怎么可以不花一两银子,就骗走了我的崇拜
我是说川西
我是说高原上的那些事情
比如四姑娘山,比如长坪沟
双桥沟或海子沟
它们这么可以这么无理
这么横行霸道
想什么时候来取我的魂魄
就什么时候来截住我向往的去路
所以我必须大声说美
搜索人间一切最精彩的
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
我必须懂得表达和称赞
以免受到她们
温柔的裹挟或粗暴的劫持
所以我必须在神山和圣水中游刃有余
否则,我的心胸将因为一时的偏狭
而永世不得安宁
高原献诗
米亚罗,天空唯一的一朵云掉进了我的眼底
三千里红叶还没有睡醒,三千里长风仍在高原之外
磨着刀剑。而在此之前,一切活着的事物
都快乐着,并且称心如意
翻过鹧鸪山就是马尔康
马背上的阳光很安静地闪亮。牦牛很安静地吃草
古老的小镇很安静地升起了炊烟
历史很安静地躺在纪念馆里,等待着不朽
车灯来不及眨一下眼睛,就把一些记忆送到了更远处
陌生的村庄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的相机
和我冲锋衣上的灰尘。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灰尘
如果我不带来,它们一定还会滞留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哪有这么清纯的一棵火苗啊
一个小女孩,在草甸上自顾自地胆小,自顾自地天真
自顾自地走入没有边际的满足与寂寞
她此刻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复杂和冰冷
就自顾自地简单起来,热起来,美起来
一匹小马和一条小溪流突然碰到了一起
马儿和溪流一样单纯,一样没有哀愁
雪山有一部分情感在融化,另一部分仍在结冰
融化是幸福的,结冰也是幸福的
每一种幸福都有自己的理由
如同每一种哀伤,都有自己的长短
青藏高原就是这样的,他不知疲倦地慈祥着
哺乳着羚羊,马匹还有牦牛。而牦牛总是喜欢
用反哺的方式将肥美的大地吊在乳头上,摇摇荡荡
像心跳一样大音稀声,梦想一样大象稀形
雪山也是这样不知疲倦地抱守着一方神秘
这怎么可以?红杉和冷松怎么可以不打招呼就把秋天
领回家中。云怎么可以不站队就涌进峡谷
怎么可以不花一两银子,就骗走了我的崇拜
我是说川西。我是说高原上的那些事情
比如四姑娘山,比如长坪沟、双桥沟或海子沟
它们这么可以这么无理,这么横行霸道
想什么时候来取我的魂魄
就什么时候来截住我向往的去路
所以我必须大声说美,搜索人间
一切最精彩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
我必须懂得表达和称赞,以免受到她们
温柔的裹挟或粗暴的劫持
所以我必须在神山和圣水中游刃有余
否则,我的心胸将因为一时的偏狭
而永世不得安宁
神山下的祈祷
羽衣霓裳。时光卸下的每一件晚装
都穿在了山身上,穿在了树身上
云走过的路也是石头走过的
水走过的路也是砂子走过的
一株枯萎的草怎么会不知道高原的海拔
终年积雪的峰峦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脸
有多美,有多丑,有多么真实和虚幻
它们怎么会不知道
荒僻是为每一个远方洞开的空门
而静谧,才是留给自己的苦衷和灿烂
四姑娘山,躲在浅水中的一头牦牛
或许正是我的前世。否则,错过了它
我就错过了你,错过了冷风里每一片叶子的晃荡
错过了羊群中每一次没有缘由的躁动
我揣测,遥望。重温一头母牛黄昏前赐与我的爱情
我在独自掌握回报和感激的动作要领
石头怀孕了,将生下更多的石头
坚硬,固执,孤傲,恢弘。像我年少时
立下的誓言。像我不知轻重时对于生命流程
草率的彩排。但这一切都不是现在
现在。我把厌恶和憎恨压得很低
将赞美和爱捧在手中,高高扬起
我在太阳的另一面埋下一颗种子
如果不是温暖,那它只能永远是石头
四姑娘山,我从哪里来你知道
石头有一颗飞翔的心,连它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而我有一颗匍匐的心
我是知道的。我匍匐在潮湿的土壤里发芽
在带刺的树枝上现蕾。我匍匐着
不和任何一棵大树一争高下
我匍匐着,其实我更想弄清自己
还能拿出多少爱来赔偿爱我的人
是的我不能不知道,当人成为佛的那一刻
他的每一个口袋里一定都装满了爱
他的心一定长成了爱的模型
而当众人成为众神的那一刻
大地也一定能复制出天堂的结果
四姑娘山,那时,请让我把骨头寄存在这里
让我的遗骸变成野草,被羊儿吃掉
变成沙棘,被鸟儿衔走
四姑娘山,我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
在我活着的时候,请让我说过的谎言被流水淹没
成为泥沙。请让我负过的心被泪珠修复
成为花蕊。请让我亏欠过的人被神圣托起
成为幸福的替身,成为高高在上的云彩
在斑斓中,继续俯视我一世的卑微
羽衣霓裳。时光卸下的每一件晚装
都穿在了山身上,穿在了树身上
云走过的路也是石头走过的
水走过的路也是砂子走过的
一株枯萎的草怎么会不知道高原的海拔
终年积雪的峰峦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脸
有多美,有多丑,有多么真实和虚幻
它们怎么会不知道
荒僻是为每一个远方洞开的空门
而静谧,才是留给自己的苦衷和灿烂
四姑娘山,躲在浅水中的一头牦牛
或许正是我的前世。否则,错过了它
我就错过了你,错过了冷风里每一片叶子的晃荡
错过了羊群中每一次没有缘由的躁动
我揣测,遥望。重温一头母牛黄昏前赐与我的爱情
我在独自掌握回报和感激的动作要领
石头怀孕了,将生下更多的石头
坚硬,固执,孤傲,恢弘。像我年少时
立下的誓言。像我不知轻重时对于生命流程
草率的彩排。但这一切都不是现在
现在。我把厌恶和憎恨压得很低
将赞美和爱捧在手中,高高扬起
我在太阳的另一面埋下一颗种子
如果不是温暖,那它只能永远是石头
四姑娘山,我从哪里来你知道
石头有一颗飞翔的心,连它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而我有一颗匍匐的心
我是知道的。我匍匐在潮湿的土壤里发芽
在带刺的树枝上现蕾。我匍匐着
不和任何一棵大树一争高下
我匍匐着,其实我更想弄清自己
还能拿出多少爱来赔偿爱我的人
是的我不能不知道,当人成为佛的那一刻
他的每一个口袋里一定都装满了爱
他的心一定长成了爱的模型
而当众人成为众神的那一刻
大地也一定能复制出天堂的结果
四姑娘山,那时,请让我把骨头寄存在这里
让我的遗骸变成野草,被羊儿吃掉
变成沙棘,被鸟儿衔走
四姑娘山,我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
在我活着的时候,请让我说过的谎言被流水淹没
成为泥沙。请让我负过的心被泪珠修复
成为花蕊。请让我亏欠过的人被神圣托起
成为幸福的替身,成为高高在上的云彩
在斑斓中,继续俯视我一世的卑微
▲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湖,她的名字叫“四姑娜措”,听起来很美,很想叫人一头扎了进去。
▲山如果高一些,就是雄伟;如果更高一些,就是巍峨;如果再高一些,就是危险和死亡了。
▲死亡是神圣而又庄严的。死亡和死而不亡究竟有什么区别,还是默默地去向佛祖请求忠告吧。
难得遇上这么好的晴天,彩林醉了,连迷雾看上去都像一条条洁白的哈达。
谁说这梦幻般的的景致不是蓝天、彩林和迷雾共同的绝作?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因为在大美面前,所有的言语都是多余的。
这两张照片的时间只隔了一天。上图是在双桥沟景区尽头拍的,下图是在长坪沟景区入口拍的。
两张照片看起来则完全是在两个不同的季节拍摄的。
这是我们的住处,明朗藏寨。老板和老板娘是一对年轻的藏族夫妻。人很热情,房间很干净,价格很公道。
明朗藏寨就在长坪沟沟口。你可以从这里乘观光车,直接走上长坪沟7公里长的栈道。
我们去长坪沟时,正好碰上了雨天,打着雨伞走在栈道上,听溪水喧腾,林涛奏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耳洞里轰鸣。
在长坪沟,如果你见到这样的蕨类、菌类或蘑菇类的东西,请不要吃惊。
因为,这里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到处都衍生着奇妙的物种。
如果你想骑马走进原始树林,抵达长坪沟尽头的木骡子景点,就必须在这个插着红旗的游客驿站租用马匹。
我们骑着马出发了,路边的小溪因为雨水而试图泛滥。
雨停了,但天空仍然阴着脸。我们的马匹刚刚翻越了一道山坡,踏上了平缓的地势。再往前走一百米,就可进入原始森林了。(图为跟在我们后边的游客)
这是我太太第一次骑马,她胆子最大,始终走在队伍前面。迎面撞来的风光让我们应接不暇。
木骡子景区到了。此时,我们才知道所谓的“木骡子”,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牧场。这让我们非常失望。
一群牦牛对我们的到来无动于衷,如同我们对名不副实“木骡子”无动于衷一样。
大雾锁住了山沟。我们的视线被挡了回来。雾里的雪山和林莽已经谢绝了我们的脚步。
我们骑着马返回驿站。一匹可爱的小马驹让我们置换了心情。
长坪沟口,谁也说不清这饮马的小溪最终会流向哪里
在四姑拉错旁,破天荒地当了一回牛仔。
一天之中,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我们在抑扬顿挫中坐着季节的过山车,体验着天堂与地狱的转换。
大家猜一猜,这四个藏人在干什么?他们背后的小石塔是做什么的?
双桥沟撵鱼坝附近,有一个漂流点。你可以在雪山融化的溪水上,把你的旧梦漂成深绿。
四姑拉错两旁,山坡上的秋草像骏马的鬃毛一样柔软、亮滑。
天蓝得像你逝去的青春,水绿得像你不曾戴过的翡翠手镯。
所有美好的时光里都有朋友的影子。
如果没有朋友,山川顿失颜色!
记住:永远也不要丢了你的朋友!
如果有朋友要丢你,你一定要打电话骂他;
如果是你丢了朋友,你一定要去朋友的家里登门赔罪!
当我们逃离了燃烧的城市
从最初的田间小路回头望去,
我说∶让草掩盖我们的脚印,
让刺耳的先知们在火中沉默,
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我们注定产生新的激烈的部族
没有邪恶和浑浑噩噩的快乐。
——米什沃:《逃离》
在我失望的一刻,我感受到鼓舞。
当我被毁坏,我同时也在康复。
当我像大地一样安静坚实,那时候
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声与众人说话。
——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
我深信野花就是众神的眼睛。什么样的势力都拦不住野花的苏醒。
这个秋天,已经有太多的野花在草甸上遇见我们,与我们相视一笑,陪我们照相留影。
正轨不一定永远都是笔直的,它一定也有自己的弧度与弯曲,
就像这里的每一条通往神灵的陌路。
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被每一条正轨的弧度和弯曲召唤着、引领着,
通向光明和美,通向爱和永生的呢?
那大美无言之处,我们称之为风情、风华、风采、风俗、风韵、风景或风光。
与正轨相对的,便是传说中的邪路或歧途,
即使没有弧度与弯曲,也一样能通往邪恶与地狱。
幸好,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里。
你知道秋风起时大地会身披金甲。
不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稍稍早了一些,
时间才刚刚进入九月中旬,
四姑娘山的山体才刚刚从大地的衣橱里翻出了第一件金甲,
只不过是随意地抖了抖,尚未来得及正式加身,
我们就已经被其灼灼光华映照得盼顾生辉了。
你知道所有凡俗的生活都是在低处展开的。
我们路过的区域,海拔一千米以下的世界通常是红尘滚滚,一片喧嚣,每一条河流都学会了说脏话。
海拔二千米以上,山河静寂,天空魅蓝,每一汪湖水都眨着清纯透明的眼睛。
我们差不多是用了半辈子的光阴,才给自己挣来这么一回做云的机会。
我们在川西高原的图案上飘来飘去,淋漓尽致。
这样的感觉,足以弥补我们的生命在平地上的所有亏空。
野花的目光是慈悲的、宁静的,心胸也必然是宽容的、明亮的。
野花肯定能记住我们的脸,只是,我们连野花的名字都没有弄清楚,
就要仓促地脱离它们的关怀,重回凡尘度日,带着低矮的欲望与蹉跎。
沙棘果熟了。这是四姑娘山一带随处可见的野果,它的味道就是川西高原的味道,有一种高深莫测的酸,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甜,还有一种鬼迷心窍的涩。
神秘的湖水,倒映着神秘的高原蓝。
树枝死而不朽,僵硬的手指直插云霄。
这里是人参果坪,双桥沟最迷人的景点之一。据说,每到夏天,野花就会在这里铺开花毯,溪水中流动的全都是花的影子。
秋色缠绵,层林尽染。我们从天而降,接受野花的引领。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我在桥上看雪山,雪在雪山上看我。
离开四姑娘山,我和老伴在途中(巴郎山垭口)留影。
一、康定呀拉索
一直觉得情歌中的康定是一匹马、一座山和一朵云的混合体,是张家溜溜的大哥和李家溜溜的大姐放映在天边的一场凡俗的爱情片,打着月亮弯弯的白色字幕。
由于遥远得不着边际,康定对我的诱惑本来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确定的。然而,跑马山不会转路却会转,铁路公路、国道省道一直都在转个不停,转着转着就把我们转到了川西。
我们看上去好像是有些被动,但实际上我们是主动的。早在两年前,我们就在成都的宽窄巷子里,在一次摄影展上锁定了康定。这个秋天,我们再度结伴而行,势必要在康定情歌的来处,像亲手抓住一匹马驹一样一把抓住康定。这一回,我们再不会让康定溜溜的城,轻易地从我们的手心和脚底下溜走。
很多年,我一直不觉得康定是一片幅员辽阔的疆域,不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地址,可以用来通信,或是朝里边喊一声就能听到许多亲切的回应。康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抽象了,它既不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也不像是爹妈生出来的,却更像是从嗓子里唱出来的,除了音调和节奏可以把握之外,就再也看不到更多具体的陈设。因此,在我懵懂的青春记忆中,康定简直就像希望一样飘忽而又渺茫。而且,我觉得它一直是侧着身子,背对着阳光在天边吃草。
实际上,真正的康定离天边很远,离成都却不到三百五十公里。真正的康定一点儿也不像情歌那么虚幻。数千年前,它曾经是古牦牛国的核心疆域;数十年前,它曾经是西康省的省会。现在,它仍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当我为了一次旅行,而刻意弄清这些地理概念与历史渊源时,我已经到了不爱唱情歌的年龄。我圆润的青春开始打折,不再是溜溜的大哥。
秋天是一个常常叫人脚板发痒的季节。每到这样的季节,我们都禁不住就会这样想:如果再不出一次远门,如果再不做一次长途跋涉,痒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去康定的理由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那天,我们在成都新南门汽车站,买好了下午一点十分去康定的车票。没想到刚刚检票上车,热情好客的成都平原,就已经搭好了广袤的戏台,准备为我们表演一出精彩的川剧。首先登台的当然是新南门汽车站,它一上台就做了一个非常滑稽的变脸动作,不由分说就将发车时间由下午一点十分变成了两点半钟,硬是让我们在臭烘烘的车内苦等了一个多钟头。等到汽车发车驶离成都市区,才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大地也开始跟着变脸了——在新津、蒲江县境内,我们看见四川盆地将屁股一撅,就撅成了丘陵;在丹棱、雅安地界,我们看见丘陵将肩膀一耸,就耸成了高山。车过雅安,318国道接着也表演起了最拿手的堵车绝技,左一堵,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右一堵,两个小时就过去了。接下来,天空也开始将蓝脸变成了黑脸。随后,车出名山,过天全,穿二郎山隧道,川西高原便在暗夜里进一步绷紧了更黑更黑的脸。黑脸左一甩右一扭的,目的地也就越来越近了。
我们一行六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近十二个小时,才把三百五十公里的距离走完。抵达康定时,无论天空和大地怎么变脸,我们都已经看不清了。直到凌晨两点钟,我们在冷风嗖嗖的康定县城下了车。寂静的街道上灯火阑珊,街道尽头的世界一片漆黑。我们一下车就迷迷糊糊地被一个藏族妇女拉进了宾馆,唯一可以看清楚的,就是她家的宾馆名叫“银华”,宾馆和折多河只隔了一排房子。夜色迷离,寒气逼人,我们还没有和高原见上一面,就已经被它折腾得筋疲力尽。幸好宾馆就在路边,省得我四处寻找,否则,我们真的会被这陌生的夜晚彻底击垮。
关上门,洗掉风尘仆仆,我们就在康定溜溜的城中睡下了。我们听不见自己的鼾声,却能听见折多河水在梦中流得无比欢畅,那汹涌的涛声,简直就是世上最亢奋的一支催眠曲。
那一夜,我们停泊在高原上的睡眠非常短促,大约不足五个钟头。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被一个康巴汉子野狼一样狂野的歌声吵醒了。呀拉索,呀拉索……
我们睁开眼睛,却仍然没有看清康定的摸样。
康定在山上站着,在河边蹲着,在树林中躲着,一直在等我们接近。
那一天,我们在新都桥餐馆里共进晚餐
那一天,我们在四姑娘山四姑拉措旁合影。左起:任哥、何太太、何蔚(楼主)、任太太、曹太太、曹总
那一天,新都桥附近,川藏路旁。藏族司机阿布的家。雨后的天空蓝得发抖。
二、去尼玛的木格措
曙光初现,又一个丰腴的早晨正从跑马山的云缝里露出了臂膀。
我在想,用丰乳肥臀来形容康定的早晨,该不会有很多人投反对票吧?不信,你去看看那些高耸的峰峦和肥硕的草甸,不用解释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撩开窗帘,仰望天空,霞光已经扭扭咧咧地泛起了胭脂红。此时此刻,我们一行人,满怀着疲惫与兴奋,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从折多河水的喧哗声中翻身起床。我们实在是太想早点看到被昨日的夜色藏在被子里的川西高原了。我们实在是太想知道,情歌中的康定,究竟长了怎样的一幅面孔。
我们三个家庭、三对夫妻,出门前就把这次旅行定性为“蜜月之旅”。我们的首选目的地便是康定木格措,然后是新都桥,然后是塔公和八美。如果天气晴好,再然后我们可能还会趁势北上,顺便看一眼道孚的玉科草原和亚拉雪山。
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朝四周张望。简短的街道和低矮的楼房,暂时无法阻挡我们的视线向远方延伸,与天际线实现对接或重叠。实际上,无论我们的视线怎样延伸,也无法逾越那些鼓胀鼓胀的,正在给云朵喂奶的山峰。它们最终只能反射回大脑,成为漫无边际的瞎想。
此时的康定依然是抽象的。唯一不抽象的是,在康定县城,我们与一位私家车主达成了一项非常具体的协议:他同意带我们走“非常路线”,去木格措景区。
所谓“非常路线”,指的就是可以逃票的路线,也是备受驴友背包客们无限爱戴和景仰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的路线,很容易激活沉睡在我们体内的冒险细胞和阶级斗志,很容易让人产生惶惶不安的兴奋感。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逃票经验的菜鸟级驴友而言,“非常路线”更是显得光芒万丈、魅力四射。难怪“逃票”两个字一说出口,立刻就有极少数机会主义分子血压乱窜、躁动不安呢!我们六个人中,至少有一半人可以归纳到“极少数”的范畴。其实这都是被高票价给逼的。凭什么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们可以随意卖来卖去,咱们就不能逃他一回票呢?
据我所知,还有一条“平常路线”,是直通着木格措景区大门的,距康定县城只有25公里,来回包车的费用也不过一百块钱左右。木格措景区门票和观光车船票加起来,差不多300来块大洋,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路线完全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像是为官僚资产阶级而专门设定的。逃票,就是对这种不合理路线最有效的否定。
就像康定曾经叫“打箭炉”一样,木格措也曾经叫“野人海”。但不管它叫什么,它现在都已经是中国高原湖泊景区中的明星大腕了,其地位与“艳照门”的主角张柏芝不相上下。我不止一次地在互联网上搜索过木格措,不止一次地在照片上见过这一片由高山海子、原始森林、草原花甸、叠瀑温泉构成的童话景观。木格措景区幅员300多平方公里,仅其中的芳草坪、七色海和杜鹃峡等处个景点,就已经不止一次地让我梦魂萦绕、血脉喷张。
打定了逃票的主意,我们就开始慌慌张张地吃早餐。康定的早餐异常单调,似乎也没有什么特色,一碗牛肉面中找不出两片牛肉,价格却比省会成都还要高。吃完早餐,抹抹嘴巴,我们就上了车。司机(车主)是个40岁左右的康巴汉子,他说,只要我们肯出600块钱租用他的车,他就可以带我们逃票,并且给我们当导游。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们最终以400块钱的价格搞定了他。
不幸的是,我们刚一上车,阳光就不见了。我们沿着没有阳光的山路蜿蜒而上,一个小时就到了亚拉神山的某个峡谷口。此时,气温已降至摄氏5度以下,天空忽然飘起了毛毛细雨。司机特意将车停在路边,让我们下车拍照。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几个老外,抢在我们之前占领了有利地形,与我们争起风光来。几个老外在刻有“亚拉神山”标志的石碑前,不停地摆姿势、做表情,我们冒雨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在石碑前留影的机会,于是,我们本能地朝老外翻了几个白眼,就重新回到了车上。
气象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华西秋雨”。这个季节,川西一带一旦下起雨来,没有十天半月是很难停息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我们就杠上了华西秋雨,这确实是一件很要命的事。如果仅仅只是小雨丝丝也就无所谓了,可问题是,就在我们到达红海草原边缘时,雨丝一眨眼就飘成了雪花。待汽车开到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红海草原中心地带时,雪花一抹脸就舞成了鹅毛大雪,气温也下降到了摄氏零度以下。我们在红海草原上喘着粗气,瑟瑟发抖。尽管我们都穿着有内胆的冲锋衣,却仍然抵挡不住突如其来的风雪。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车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红海子朦胧的背影,举着相机却无心拍照。
木格措就这样将我们逐出了它的领地。我们付给藏族司机的导游费也一并打了水漂。
活该!为什么不选一个对的时间和对的路线呢?——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木格措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那就——去尼玛(你妈)的木格措吧!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在心里骂着。
只有天知道,其实我们是在骂自己。
听说新都桥是摄影家的天堂,果然名不虚传。坐在车上,随便往窗外一照,就可以抓到一大堆美景
那一天,在道孚县八美镇街头,阳光当顶照射,艳气逼人。左起:何太太、何蔚(楼主)、曹太太、曹总
那一天,我们三个家庭、三对夫妻,一行六人在四姑娘山脚下合影留念。
看一个个傻头傻脑滴!
上图:雅拉神山
中图:雅拉神山下的溪流
下图:海拔4200米的红海草原(去木格措遭遇大雪)
上图:大雪,红海草原上的心形海子中图:牧场围栏
下图:新都桥途中的草甸 (哦,很抱歉!遭遇大雪,无心拍照,随便弄几张应付应付)
去新都桥的途中,山坡下的藏族民居。随手拍。
三、新都桥,九月的电热毯
新都桥是不是一座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是一座海拔三千三百米以上的高原小镇。川藏公路南线和北线在此交汇分岔,像两条张开的布袋口,将康定以西的雪域风光尽收囊中。如果不是一拨又一拨背包客在进藏或入滇的途中遇见了新都桥,如果不是数码相机和互联网替高原上空的飞鸟说出了真相,谁也不会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巴小镇,究竟埋藏有多少美的秘密。
我们是从康定县城直接奔新都桥而来的。那天在木格措,雨和雪左右开弓,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逃窜。当汽车从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红海草原一路滑到半山腰时,我捂着被雨雪扇得发烫的脸对同伴们说了声:还是去新都桥吧!于是,我们就回到了康定溜溜的城,退掉了溜溜的房,重新叫了一辆溜溜的面包车。那一天,一切都是溜溜的,除了心情。
我们沿着川藏公路(318国道)折多山段逶逦而行,一路辗转、盘旋,高处白雪皑皑,低处细雨濛濛。八十公里的路程,竟然耗费了我们四个小时的光阴。到达新都桥时,天依然吊着那张又长又灰的老脸。雨越下越有激情。
我们撑起雨伞,跳下车,在恍若隔世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行走,步子迈得稍快一点,就会让人感到心跳气喘,头晕目眩。我想,若是没有华西秋雨,九月的新都桥本应该是一片灿烂辉煌的光影世界,与天堂的模样不相上下吧?况且,一年四季,川西高原上所有的雪山、草甸、峡谷、河流、湖泊、树林和村庄的静美、秀美、壮美,以及原始之美、自然之美、神秘之美、古朴之美,差不多全都集成在它的身上,无论是一起一伏,一颦一笑,还是一弯一拐,都备受中外驴友和摄影爱好者们的热捧。我甚至是在还没有找到爱它的理由之前,就已经莫名其妙地爱上它了。可是,在雨中,我左顾右盼,却怎么看也看不到一个“新”字——这里的桥是旧的,街道也是旧的。这里的房屋即使是新的,但由于石块筑成的墙壁没有经过粉刷,看上去也依然是旧的。更有趣的是,这里的旧似乎与岁月无关,与历史无关。这里的旧,是无法描述的那种旧,在单纯与简陋之间,在丰富与驳杂之间,交叉重叠着,叫人无法理顺自己的思绪。
所以我宁愿相信这就是神秘本身。要知道,新都桥还有一个相当欧化的名字,叫“东俄罗”,谁也说不清“东俄罗”这个神秘的符合中究竟藏有怎样的况味。
在二郎山外的公路向甘孜境内伸过手来之前,“东俄罗”一直是睡着的,它不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怎么认识它。是川藏公路一把拽醒了它,让它站了起来,动了起来。当川藏公路继而又从汉语词典中将“旅游”这个词带到藏区时,它才猛然醒悟到,原来这个世上不只有牦牛、马匹和羊群的脚印,不只有青稞酒、酥油茶和糌粑的气味,还有那么多眼花缭乱的时装、食物、手机和钞票在四处招摇,还有那么多红男绿女在天地间纵情穿梭。从此,寂静闭塞的“东俄罗”改头换面,雪藏了自己的乳名,开始干起了旅游接待的营生。当然,客栈林立的新都桥从此也患上了难以治愈的失眠症,永远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拥有羊羔一般恬静的深度睡眠。
那天,我在秋雨中仔细地打量着新都桥,试图找到我在图片上见过的某个标志性画面,找到某个似曾相识的镜头,或是与我的想象相吻合的对接点。但是,我在镇子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因此,新都桥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相当模糊的,再加上高原反应从中作梗,就不得不令人产生出许多幻觉,譬如:这是不是一座神经错乱的小镇啊?蓝天是不是放了长假?白云是不是罢了工?到处都是空落落的,湿淋淋的,晕乎乎的,偶尔还有乌鸦从路边的白杨树上扔下几声聒噪,引起我们这些外来人一阵阵耳鸣。这时侯,就连雨声也开始变调,纷纷将清脆的滴答改成了沙哑的颤悠,我们的心情随着雨水的颤悠而继续下沉,很快就沉到了失望的谷底。
天黑前,我们热切期盼这雨哪怕暂停片刻也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街道上,从容地走上一个来回,将新都桥的新与旧看得更加清晰。然而,这么简单的愿望终究还是遭到了雨的回绝。我们仍不死心,执意在雨中转了一圈,谁也不愿意待在宾馆里束手就擒。我们就这样皱着眉头从西走到东,目睹着白杨树和高原柳在雨水中淋浴。目睹着形形色色的藏寨客栈挂着形形色色的招牌,沿川藏公路一字排开,在鲜花和树丛中守株待兔。朦胧中,那些裹着暮气的山峦,依然是草色弥天。山坡上的经幡和六字箴言,依然是庄严肃穆。从镇子中间流过的小河,依然是浑浊而又肤浅。
我们心里很清楚,是雨水打翻了季节的调色板,扰乱了美的秩序,让高原的画布颜面尽失,让仁慈敦厚的天空面目狰狞。不过,雨水毕竟不是常态,雨水背后的晴空才是。晴空之下,新都桥的另一身装束,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如果不尽早出现,那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绕开它,直接去一个没有雨水的城,或是去一座阳光普照的山,与清朗的秋风握手言欢。
但此刻,我们停在了新都桥,我们只能被雨水牵着手东游西荡。泥浆溅到鞋面和裤腿上,冷风呼呼地撞向胸口。转眼间,天就要黑了。我们在镇上找一家干净的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就住进了一家汉族宾馆,准备等到来日,看看天气再决定去留。
九月的新都桥昼夜温差极大,尤其在下雨的夜晚,寒冷和潮湿同时要来敲门,生活中就不得不多出了一些防范。听说,就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已经下过雪了,这时候,所有的宾馆客栈都用起了电热毯。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但仔细一想,若是不用电热毯,你疲惫的身体或许在一夜之间,就会被潮湿的床单读一千遍,直到把你唐诗一样的关节读出风湿来。想想风湿这狗东西虽然很是令人生畏,可这毕竟是在九月啊,出发的时候我还穿着T恤衫,总不至于一嗅到风湿的气味就无条件地向电热毯叩头吧?很抱歉,我做不到。那一夜,我用冰冷的身体挡住了电热毯的诱惑。
冷雨敲窗的声音一直持续到天明。半夜里,一群喝了酒的藏族青年跑到宾馆来闹事,他们踢着房门大呼小叫,和汉族老板胡搅蛮缠了很久,才意犹未尽地离去。之后,雨声、耳鸣声和粗野的脚步声开始纠集在一起,剥夺了我们做梦的权利。次日一早,我们去意已决,不管折多山下这座康巴小镇是不是“摄影家的天堂”,是不是户外发烧友的集散地,是不是东俄罗或者新都桥,都已经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马上就要改变行程,向不受雨水困扰的丹巴和小金一线靠拢。
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向北,向东。我们的脚步将在川西版图上划一个巨大的椭圆。
那一天,新都桥至八美的途中,藏族司机带我们去他所在的村庄。
图为搭顺风车去塔公寺拜佛的两位藏族姐妹,她们是新都桥藏族中学的学生,家在理塘。
藏族司机“阿布”家门前的围籬。雨后的雾气在附近的山顶上蒸腾。
这地方很适合逃婚。
那一天,藏族司机“阿布”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子、农具、机械。
阿布的母亲很友善地和我们打招呼,目送我们出村。
四、阳光在撒谎
那天,雨水出乎意料地倒挂在了新都桥上空。千山虚寂,万谷静笃,又一个新鲜的早晨正从川西高原上腾云驾雾而至。我们看见了。
早起的乌鸦在窗外的白桦树上呻吟了很久,还有一些别的什么鸟,也跟着乌鸦一起应和——它们说的是藏文呢还是汉语呢?这悲怆的嘀咕声令人顿生惆怅。我们听见了。
收拾好了行李,吃完早餐,我们准备立刻就弃新都桥而去。就在此时,天空的大脑里突然闪出了放晴的念头。在飘着经幡的山顶和屋顶上,大朵大朵的云不经意间就裂开了一条条缝隙,顿时就有清风朝缝隙中注入了一片片幽蓝。但这一切都留不住我们了。我们相信,比红萝卜还要新鲜的早晨明天还会有的,在丹巴藏寨或日隆藏寨,我们肯定还有机会将同样的早晨从地平线上连根拔起,抛向我们无限敬仰的高空。所以,我们对新都桥没有过多的留恋。我们将搜寻的目光再次转向了新都桥北边的八美和东边的丹巴。
从康定到新都桥,再从新都桥到八美,其间的距离差不多是相等的。散落在山坡和沟谷边的马匹、牦牛和羊群们,它们仿佛占尽了天下的祥和,它们粉红的奶头下吊着漫不经心的原野,日月星辰都像铃铛一样被它们反复摇响。这时,你会想起“岁月静好”之类的有气无力词句,想起无聊的诗歌和神圣的经典。如果此时天空是新的,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只是,在新和旧转换的过程中,说不定你忽然就消失了、遁形了,像露珠一样在人间蒸发。你说不定会脱胎换骨,被另一个自己替代。然后,天的尽头就有了你的飘泊。啊,是这样的——云在云中,雨在雨中,梦在梦中,真实在真实中。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
那天,我们在离开新都桥之前,险些遭到了一群康巴汉子的围攻。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里的藏人根本不和汉人讲什么和谐。在康巴藏区,由于许多地方不通公汽,租车就成了游客们出行的唯一选择。平时,新都桥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中转站,街头常常泊满了形形色色的私车,车主们人多势众,整天坐守街头,虎视眈眈,称雄一方。你只要和其中任何一位车主接洽,都有可能引来一群同伙的参和。如果你势单力薄,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受到威胁、挑衅和敲诈。近几年来,新都桥已经成了许多驴友的伤心之地,没想到我们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凶险,如果不是一位八美的司机帮我们解围,很难预料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那是一段无聊的插曲,颠来倒去地将我们纠缠了很久。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脱身,许多问题都没来得及弄清楚,我们就登上了另一辆去八美的汽车。与我们同时登上汽车的,还有两位腼腆的藏族少女,她们是理塘县人,在新都桥藏族中学就读。她们要搭我们的顺风车去塔公寺拜佛。乌鸦的叫声始终挥之不去。天空呈现出一片片零碎的瓦蓝和羊脂白,云朵和霞光同样挥之不去。
在车上,我听见两位藏族少女管司机叫“阿布”。头发蓬乱的“阿布”挂着两张油黑的刀形脸,他驾驶的五菱面包车正以60码左右的速度,迎面撞向川藏公路北线的一道道风景。公路两旁的青稞刚收割不久,金黄的麦茬为起伏不定的坡地保留了均匀的暖色;沿途的山势如同马背一样平滑而又富有光泽;雨后的河流水位陡涨,波浪覆盖了秋色初染的河床,同时也揉碎了一切事物的倒影。所以,就在黑脸“阿布”带我们绕进村庄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
黑脸“阿布”并不是刻意要带我们去参观他的家,而是因为他的手机忘在了家中。他一点也不在乎这样做是否会耽误我们的时间。黑脸“阿布”的家坐落在平坦的山脚下,两栋石头砌成的小楼,一栋坐北朝南,一栋坐西朝东,一条水泥路直接铺到了大门口,树枝编织的围篱将菜地与水泥路隔开,让传统生活与现代气息互不干扰。树叶刚刚被秋风熏出了黄边的钻天杨,在房前、屋后和路边站得十分随意,一条又清又浅的小溪扭着水蛇腰正要从它们的胯裆下溜走。
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我开始怀疑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事物。我开始怀疑一切的真实。因为那一天,天气预报撒谎了,雨水撒谎了,阳光也撒谎了。天空一会儿蓝一会儿灰,云朵一会儿轻一会儿重,我一会儿聪明一会儿糊涂。我看不见远方,远方被搁置在雪山顶上。我所能看见的近处,山却是魔幻的,拥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炊烟和牛粪;水是魔幻的,拥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清澈和浑浊。那一刻,我怀疑门槛却相信窗子,我怀疑汽车喇叭却相信流水潺潺,我怀疑路途逶迤却相信雾气弥漫,我怀疑树枝摇曳却相信草色匍匐。
因为那一天,眼睛撒谎了,呼吸也撒谎了,唯有饥肠在肚子里说了几句真话。
新都桥到八美的路边,收割后的金色的青稞地,倒映在雨水中的白云后蓝天。这一带,随处都有迷人的景色。
这些片子都是隔着车窗随时拍滴。
如诗如画的村庄,如花似玉的原野,在川藏路两旁静谧着、灿烂着、缤纷着。
不禁会想:若是在这样的村子里找个相好,结果会怎么样呢?
在新都桥一带,你不得不承认,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书写着精彩的童话,每一片天空都吟诵着动人的传说。
那一天,我们的旅程晴过,阴过,雨过,雪过。
那一天,川西高原在不断地为我们变换着丰富的面部表情。
上图:塔公草原,金色的塔尖仿佛与远山的雪线等高
中图:丰收后荒凉的土地,经幡在飘摇
下图:道孚县八美镇乾宁村。送我们去丹巴的司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
五、八美是什么美
说起八美,忽然就明白了:美其实是一种常常让人感到饥饿的暗示。正因为有这样的暗示,我们才会加倍喜欢上路的感觉。在路上,美要么是迎面扑来,要么是我们迎面扑向她,那种填不满的饥饿,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饥饿。况且,川西高原上的每一座山都像图钉一样,将美稳稳地钉在地上,风吹不动,水冲不走。况且,在新都桥以北,穿过塔公草原,进入道孚县境内,还有一个名叫“八美”的好地方——呵呵,一个美就足以要人的命了,更何况是八美噢!
新都桥是汉语的新都桥,一说你就能听懂。可八美毕竟是藏语的八美,地地道道的藏语,不是谁都可以听懂的。所以,一路上我始终不敢相信这是在九月,触地即化初雪刚刚涂改了狼毒花的色彩。我不相信一件衬衣,已经裹不住午后的温度。冷开始在神经末梢上停顿下来。
整整四天,我们不停地在路途上奔波,直到可以乌鸦交换歌声,和云朵交换眼神。耳鸣的时候,我更能听见车窗外一闪而过的草原正在哈哈大笑,笑季节的荒诞和牛羊的憨实。而泥土,则依然是一声不吭地想着春天的往事。中度的高原反应,使我不敢相信许多真实的事物,它们总是晃来晃去的,犹如乱花迷人眼。而我在想,再过十天半月,几场雨滋过来,几阵风刷过来,草色就不再绿了,更多的冷空气就有了翻山越岭大动作。我不敢相信到了那个时候,塔公草原的秀发上还能留下几朵情人的插花。我只能说——八美,不管它的脸上有多少条皱纹或是有多少颗青春痘,可它都是八美;不管它的土地有多么瘠薄或是有多么肥胖,可它首饰盒里的金银珠宝,都不会少掉一个数字。
汽车在川藏公路北线噗噗奔驰,草原雪峰历历在目,塔公到了,八美也近了。
按照藏语的说法,塔公意为“菩萨喜欢的地方”。菩萨都喜欢的地方,人当然是更喜欢了。传说塔公曾经是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时走过的路段,山坡上漂浮的云朵中,说不定还游曳着公主沉鱼落雁芳魂呢。川西高原到了塔公这里,海拔高度已经升至3700米以上,黑色柏油路宛如黑色牛皮带一样束紧了大地的腰身,使得塔公草原更加英姿勃发,傲气逼人。这时候,塔公寺金色的塔尖显得格外耀眼,远远地看上去,白雪皑皑的雅拉神山与塔尖之间,仿佛暗藏着一条神秘的等高线。我不想知道究竟是谁刻意制造了这种奇特的视觉效果,我宁愿相信,这是人与神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
在得不到官方媒体关注的前提下,多年来,塔公和八美完全凭着自身的天生丽质,在背包客的长短镜头和日志攻略中悄然鹊起,成为川西高原上最知名的小镇之一。而在此之前,它们不止一次地蒙受神灵点化,所以,你应该相信,草原有耳朵,听得见昆虫唱歌;草原有鼻子,分得清牛和马的汗味,分得清藏人和汉人的体气。我们是汉人,虽然在新都桥熏染了一夜的藏香,可草原依然认出了我们。草原说,拿钱来吧,我让你看个够!马儿说:拿钱来吧,我让你骑个够!可我们还是下意识地捂紧了钱袋,准备抢在下雨之前扬长而去。
我们只在塔公草原边缘停留了十几分钟。看看天,九月中旬的天仍然大面积地阴着,不过天色还早,还不到正午。再看看地,刚刚和夏天分道扬镳的地,上面已经积满了雨水和雪水。最后,我们再看了看苍茫无际的草原,忽然间我们发现,那些被牛羊啃噬和人畜践踏过的草,正在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初雪后的天空亮出了拚命的一绿。
我们知道,那是春天的回光返照。
继续向北。路过土石林,八美正在八里之外等着我们。
没过多久,汽车又像减免债务一样,豪爽地替我们减掉了这最后八里山路。一拉开车门,正午的阳光“嗖”地一声就与我们撞了个满怀,高深莫测的八美也“嗖”地一声站到了我们面前。
一连几天没有见到太阳,到了八美镇,我们一下车就被高原上野性十足的太阳给撞晕了,连眼睛都睁不开。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八美的阳光至少有八两重,那张辉煌的大巴掌一搧过来,我们的脸上立马就留下了一道红印子。
立足未稳,我就开始眯着眼睛朝四周张望,然后,我试着问自己:八美究竟是什么美呢?我一时难以对答。我只能告诫自己,八美只不过是我们去丹巴的一个中转站,据说它曾经是老乾宁县的县城,但对于它,我们的确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我们只是从它的门前路过,只是在它的地盘上转一趟车而已。在我朦胧的印象中,八美仅仅只是一个镇子、一条小街、一座寺庙、一群喇嘛;仅仅只是一场法会、一堆香火、一座村庄、一片树林而已……总而言之,八美不是汉家的公主,不是藏家的外孙,而是川西高原上一道道山梁和一条条沟壑的活体标本,人和牲口,庄稼和草,经幡和云朵,永在其中,来来往往,生生死死,川流不息。
八美不承当任何一种具体的美,它是上苍馈赠给川西高原的一枚橡皮图章,可以为一切看不见的美提供担保,也可以为一切看得见的美签字画押。
甲居藏寨:挂在天边的彩色唐卡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小的县城,它很安静地躺在大渡河谷,四面都是高山,它刻意把自己放了在最谦卑的位置。这个县名叫丹巴,县城名叫章谷。身高:海拔1800米左右。民族:藏。出生年月不详。
在这里,如果你看见阳光给雪山镀金,雪山反过来又给村庄戴上一顶童话的白帽子;如果你看见秋风将青青水果擦红,水果反过来又给门窗挂好了铃铛,你就不会怀疑,丹巴藏寨绝对是中国最美的乡村!
门前挂满了苹果、路边开满了格桑花的村庄,彩虹和霞光的村庄,你走着走着它就会让你飞起来的村庄——
甲居藏寨。云抱着它,雾楼着它,树摇着它,水捧着它……
它是一幅高挂在天边的唐卡。
碉楼在天堂里静谧,经幡在云雾中祈祷。
众人的心愿和众神的箴言,在空气中悄悄传递。
在这里,在这样的时刻,
你走过的路上不会留下脚印,
就像鸟儿飞过的天空不会留下痕迹。
这就是丹巴民居,你可以称它为藏寨或者碉楼。
你来到这里,但这不是你的家。
而当你离去的时侯,你的身体可以带走,
梦却只能永远留在这里了。
寻找你的梦,或许就是你下一次来此故地重游的理由。
高处不胜寒——这是谁说的?其实高处也有暖,既有在暖中茁壮成长的玉米,
更有在暖中无限膨胀的希望。
玉米和希望本来是毫不相干的,
因为你的到来,它们便有了本质的关联。
嗯,这多么好!
啃着亲手从树上摘来的果实,在石头上走一走,在树墩上坐一坐,
在风景中笑一笑,如果还不能满足,那你就真的是贪婪了。
——你要知道,有时候,平民的幸福,也是会让帝王们羡慕的哦!
这一天,我们用偷苹果的手给正在老去的日子抹上了一层釉彩。——想一想,幸福其实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啊!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竟然可以让我们辛苦一辈子,复杂一辈子。
一个傻子问聪明人:永远有多远?聪明人无言以对。
我曾经是那个傻子,但现在,我又成了聪明人。
当村庄、道路和山都来逼问我永远有多远时,我同样是无言以对,只好直接朝它们走过去。
山坡,寂寞的;碉楼,寂寞的;天空,寂寞的;如果一生中,你的心仅仅只拥有一刹那真正的宁静,
那么,整个世界都会是寂寞的寂寞的——就像永远
——就像无数个刹那,为你竖在了那儿。
那么,谁是刹那?谁又是永远?
你的爱人肯定知道。还有这些花朵,它们肯定知道。
花朵在刹那间开放,在永远中凋零。
爱人也是这样的。所以,从今天起,
你必须加倍地珍惜她。必须,加倍地!
此刻,我好奇地凝望着这一座废弃的碉楼,
它什么也没有说,也不知道什么是刹那,什么是永远。
它只是为自己的存在。它很有尊严地站在悬崖边,
让刹那和永远,都找不到冒犯它的借口。
在丹巴,在甲居藏寨,时间变得很有弹性。
在很有弹性的时间里,我们发现:换一个角度看刹那,
刹那是被云雾笼罩的山峰;
换一种心情看永远,永远是被众山挽留的烟云。
来自亚肖神山上的风,不知不觉就能将青青水果擦红、擦黄
卡帕玛雪峰在云中隐隐约约
接下来,是关于米亚罗和四姑娘山的文字,配图是用三洋DV摄像机拍的,画质不太好,但美色不减。
而你读到的文字,将会更优美,更变态——我能保证!!
(更多内容请看我的博客)
日隆镇日隆村,四姑娘山风景区游客中心所在地
▲四川理县米亚罗至马尔康路边风光
天空唯一的一朵云掉进了我的眼底,米亚罗
三千里红叶还没有睡醒,三千里长风
仍在高原之外磨着刀剑。而在此之前
一切活着的事物都快乐着,并且称心如意
▲小金县两河口镇,红军长征时“两河口会议”旧址
翻过鹧鸪山就是马尔康
马背上的阳光很安静地闪亮
牦牛很安静地吃草
古老的小镇很安静地升起了炊烟
历史很安静地躺在纪念馆里,等待着不朽
▲四姑娘山下的日隆镇长坪村
车灯来不及眨一下眼睛
就把一些记忆送到了更远处
陌生的村庄停了下来
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的相机
和我冲锋衣上的灰尘
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灰尘
如果我不带来
它们一定还会滞留在别的地方
▲在长坪沟口抓拍到的藏族小妹妹
别的地方哪有这么清纯的一棵火苗啊
自顾自地胆小,自顾自地天真
自顾自地走入没有边际的满足与寂寞
她此刻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复杂和冰冷
就自顾自地简单起来,热起来,美起来
▲黄昏时分,几匹马在长坪沟口准备过河
不知名的溪流和不知名的马儿
一样没有哀愁
雪山有一部分情感在融化
另一部分仍在结冰
融化是幸福的,结冰也是幸福的
每一种幸福都有自己的理由
如同每一种哀伤,都有自己的长短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色的牦牛,以前只见过黑色的
青藏高原是慈祥的
她哺乳着羚羊,马匹,还有牦牛
而牦牛总是喜欢用反哺的方式
将肥美的大地吊在乳头上,摇摇荡荡
像心跳一样大音稀声
像梦想一样大象稀形
▲四姑娘山有60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这只是其中之一
雪山不知疲倦地抱守着一方神秘,这怎么可以
红杉和冷松怎么可以不打招呼就把秋天
领回家中。云怎么可以不站队,就涌进峡谷
怎么可以不花一两银子,就骗走了我的崇拜
我是说川西
我是说高原上的那些事情
比如四姑娘山,比如长坪沟
双桥沟或海子沟
它们这么可以这么无理
这么横行霸道
想什么时候来取我的魂魄
就什么时候来截住我向往的去路
所以我必须大声说美
搜索人间一切最精彩的
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
我必须懂得表达和称赞
以免受到她们
温柔的裹挟或粗暴的劫持
所以我必须在神山和圣水中游刃有余
否则,我的心胸将因为一时的偏狭
而永世不得安宁
高原献诗
米亚罗,天空唯一的一朵云掉进了我的眼底
三千里红叶还没有睡醒,三千里长风仍在高原之外
磨着刀剑。而在此之前,一切活着的事物
都快乐着,并且称心如意
翻过鹧鸪山就是马尔康
马背上的阳光很安静地闪亮。牦牛很安静地吃草
古老的小镇很安静地升起了炊烟
历史很安静地躺在纪念馆里,等待着不朽
车灯来不及眨一下眼睛,就把一些记忆送到了更远处
陌生的村庄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的相机
和我冲锋衣上的灰尘。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灰尘
如果我不带来,它们一定还会滞留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哪有这么清纯的一棵火苗啊
一个小女孩,在草甸上自顾自地胆小,自顾自地天真
自顾自地走入没有边际的满足与寂寞
她此刻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复杂和冰冷
就自顾自地简单起来,热起来,美起来
一匹小马和一条小溪流突然碰到了一起
马儿和溪流一样单纯,一样没有哀愁
雪山有一部分情感在融化,另一部分仍在结冰
融化是幸福的,结冰也是幸福的
每一种幸福都有自己的理由
如同每一种哀伤,都有自己的长短
青藏高原就是这样的,他不知疲倦地慈祥着
哺乳着羚羊,马匹还有牦牛。而牦牛总是喜欢
用反哺的方式将肥美的大地吊在乳头上,摇摇荡荡
像心跳一样大音稀声,梦想一样大象稀形
雪山也是这样不知疲倦地抱守着一方神秘
这怎么可以?红杉和冷松怎么可以不打招呼就把秋天
领回家中。云怎么可以不站队就涌进峡谷
怎么可以不花一两银子,就骗走了我的崇拜
我是说川西。我是说高原上的那些事情
比如四姑娘山,比如长坪沟、双桥沟或海子沟
它们这么可以这么无理,这么横行霸道
想什么时候来取我的魂魄
就什么时候来截住我向往的去路
所以我必须大声说美,搜索人间
一切最精彩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量词
我必须懂得表达和称赞,以免受到她们
温柔的裹挟或粗暴的劫持
所以我必须在神山和圣水中游刃有余
否则,我的心胸将因为一时的偏狭
而永世不得安宁
神山下的祈祷
羽衣霓裳。时光卸下的每一件晚装
都穿在了山身上,穿在了树身上
云走过的路也是石头走过的
水走过的路也是砂子走过的
一株枯萎的草怎么会不知道高原的海拔
终年积雪的峰峦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脸
有多美,有多丑,有多么真实和虚幻
它们怎么会不知道
荒僻是为每一个远方洞开的空门
而静谧,才是留给自己的苦衷和灿烂
四姑娘山,躲在浅水中的一头牦牛
或许正是我的前世。否则,错过了它
我就错过了你,错过了冷风里每一片叶子的晃荡
错过了羊群中每一次没有缘由的躁动
我揣测,遥望。重温一头母牛黄昏前赐与我的爱情
我在独自掌握回报和感激的动作要领
石头怀孕了,将生下更多的石头
坚硬,固执,孤傲,恢弘。像我年少时
立下的誓言。像我不知轻重时对于生命流程
草率的彩排。但这一切都不是现在
现在。我把厌恶和憎恨压得很低
将赞美和爱捧在手中,高高扬起
我在太阳的另一面埋下一颗种子
如果不是温暖,那它只能永远是石头
四姑娘山,我从哪里来你知道
石头有一颗飞翔的心,连它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而我有一颗匍匐的心
我是知道的。我匍匐在潮湿的土壤里发芽
在带刺的树枝上现蕾。我匍匐着
不和任何一棵大树一争高下
我匍匐着,其实我更想弄清自己
还能拿出多少爱来赔偿爱我的人
是的我不能不知道,当人成为佛的那一刻
他的每一个口袋里一定都装满了爱
他的心一定长成了爱的模型
而当众人成为众神的那一刻
大地也一定能复制出天堂的结果
四姑娘山,那时,请让我把骨头寄存在这里
让我的遗骸变成野草,被羊儿吃掉
变成沙棘,被鸟儿衔走
四姑娘山,我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
在我活着的时候,请让我说过的谎言被流水淹没
成为泥沙。请让我负过的心被泪珠修复
成为花蕊。请让我亏欠过的人被神圣托起
成为幸福的替身,成为高高在上的云彩
在斑斓中,继续俯视我一世的卑微
羽衣霓裳。时光卸下的每一件晚装
都穿在了山身上,穿在了树身上
云走过的路也是石头走过的
水走过的路也是砂子走过的
一株枯萎的草怎么会不知道高原的海拔
终年积雪的峰峦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脸
有多美,有多丑,有多么真实和虚幻
它们怎么会不知道
荒僻是为每一个远方洞开的空门
而静谧,才是留给自己的苦衷和灿烂
四姑娘山,躲在浅水中的一头牦牛
或许正是我的前世。否则,错过了它
我就错过了你,错过了冷风里每一片叶子的晃荡
错过了羊群中每一次没有缘由的躁动
我揣测,遥望。重温一头母牛黄昏前赐与我的爱情
我在独自掌握回报和感激的动作要领
石头怀孕了,将生下更多的石头
坚硬,固执,孤傲,恢弘。像我年少时
立下的誓言。像我不知轻重时对于生命流程
草率的彩排。但这一切都不是现在
现在。我把厌恶和憎恨压得很低
将赞美和爱捧在手中,高高扬起
我在太阳的另一面埋下一颗种子
如果不是温暖,那它只能永远是石头
四姑娘山,我从哪里来你知道
石头有一颗飞翔的心,连它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而我有一颗匍匐的心
我是知道的。我匍匐在潮湿的土壤里发芽
在带刺的树枝上现蕾。我匍匐着
不和任何一棵大树一争高下
我匍匐着,其实我更想弄清自己
还能拿出多少爱来赔偿爱我的人
是的我不能不知道,当人成为佛的那一刻
他的每一个口袋里一定都装满了爱
他的心一定长成了爱的模型
而当众人成为众神的那一刻
大地也一定能复制出天堂的结果
四姑娘山,那时,请让我把骨头寄存在这里
让我的遗骸变成野草,被羊儿吃掉
变成沙棘,被鸟儿衔走
四姑娘山,我还有一些未了的心愿
在我活着的时候,请让我说过的谎言被流水淹没
成为泥沙。请让我负过的心被泪珠修复
成为花蕊。请让我亏欠过的人被神圣托起
成为幸福的替身,成为高高在上的云彩
在斑斓中,继续俯视我一世的卑微
▲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湖,她的名字叫“四姑娜措”,听起来很美,很想叫人一头扎了进去。
▲山如果高一些,就是雄伟;如果更高一些,就是巍峨;如果再高一些,就是危险和死亡了。
▲死亡是神圣而又庄严的。死亡和死而不亡究竟有什么区别,还是默默地去向佛祖请求忠告吧。
难得遇上这么好的晴天,彩林醉了,连迷雾看上去都像一条条洁白的哈达。
谁说这梦幻般的的景致不是蓝天、彩林和迷雾共同的绝作?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因为在大美面前,所有的言语都是多余的。
这两张照片的时间只隔了一天。上图是在双桥沟景区尽头拍的,下图是在长坪沟景区入口拍的。
两张照片看起来则完全是在两个不同的季节拍摄的。
这是我们的住处,明朗藏寨。老板和老板娘是一对年轻的藏族夫妻。人很热情,房间很干净,价格很公道。
明朗藏寨就在长坪沟沟口。你可以从这里乘观光车,直接走上长坪沟7公里长的栈道。
我们去长坪沟时,正好碰上了雨天,打着雨伞走在栈道上,听溪水喧腾,林涛奏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耳洞里轰鸣。
在长坪沟,如果你见到这样的蕨类、菌类或蘑菇类的东西,请不要吃惊。
因为,这里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到处都衍生着奇妙的物种。
如果你想骑马走进原始树林,抵达长坪沟尽头的木骡子景点,就必须在这个插着红旗的游客驿站租用马匹。
我们骑着马出发了,路边的小溪因为雨水而试图泛滥。
雨停了,但天空仍然阴着脸。我们的马匹刚刚翻越了一道山坡,踏上了平缓的地势。再往前走一百米,就可进入原始森林了。(图为跟在我们后边的游客)
这是我太太第一次骑马,她胆子最大,始终走在队伍前面。迎面撞来的风光让我们应接不暇。
木骡子景区到了。此时,我们才知道所谓的“木骡子”,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牧场。这让我们非常失望。
一群牦牛对我们的到来无动于衷,如同我们对名不副实“木骡子”无动于衷一样。
大雾锁住了山沟。我们的视线被挡了回来。雾里的雪山和林莽已经谢绝了我们的脚步。
我们骑着马返回驿站。一匹可爱的小马驹让我们置换了心情。
长坪沟口,谁也说不清这饮马的小溪最终会流向哪里
在四姑拉错旁,破天荒地当了一回牛仔。
一天之中,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我们在抑扬顿挫中坐着季节的过山车,体验着天堂与地狱的转换。
大家猜一猜,这四个藏人在干什么?他们背后的小石塔是做什么的?
双桥沟撵鱼坝附近,有一个漂流点。你可以在雪山融化的溪水上,把你的旧梦漂成深绿。
四姑拉错两旁,山坡上的秋草像骏马的鬃毛一样柔软、亮滑。
天蓝得像你逝去的青春,水绿得像你不曾戴过的翡翠手镯。
所有美好的时光里都有朋友的影子。
如果没有朋友,山川顿失颜色!
记住:永远也不要丢了你的朋友!
如果有朋友要丢你,你一定要打电话骂他;
如果是你丢了朋友,你一定要去朋友的家里登门赔罪!
当我们逃离了燃烧的城市
从最初的田间小路回头望去,
我说∶让草掩盖我们的脚印,
让刺耳的先知们在火中沉默,
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
我们注定产生新的激烈的部族
没有邪恶和浑浑噩噩的快乐。
——米什沃:《逃离》
在我失望的一刻,我感受到鼓舞。
当我被毁坏,我同时也在康复。
当我像大地一样安静坚实,那时候
我便可以用低低的雷声与众人说话。
——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
我深信野花就是众神的眼睛。什么样的势力都拦不住野花的苏醒。
这个秋天,已经有太多的野花在草甸上遇见我们,与我们相视一笑,陪我们照相留影。
正轨不一定永远都是笔直的,它一定也有自己的弧度与弯曲,
就像这里的每一条通往神灵的陌路。
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被每一条正轨的弧度和弯曲召唤着、引领着,
通向光明和美,通向爱和永生的呢?
那大美无言之处,我们称之为风情、风华、风采、风俗、风韵、风景或风光。
与正轨相对的,便是传说中的邪路或歧途,
即使没有弧度与弯曲,也一样能通往邪恶与地狱。
幸好,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里。
你知道秋风起时大地会身披金甲。
不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来得稍稍早了一些,
时间才刚刚进入九月中旬,
四姑娘山的山体才刚刚从大地的衣橱里翻出了第一件金甲,
只不过是随意地抖了抖,尚未来得及正式加身,
我们就已经被其灼灼光华映照得盼顾生辉了。
你知道所有凡俗的生活都是在低处展开的。
我们路过的区域,海拔一千米以下的世界通常是红尘滚滚,一片喧嚣,每一条河流都学会了说脏话。
海拔二千米以上,山河静寂,天空魅蓝,每一汪湖水都眨着清纯透明的眼睛。
我们差不多是用了半辈子的光阴,才给自己挣来这么一回做云的机会。
我们在川西高原的图案上飘来飘去,淋漓尽致。
这样的感觉,足以弥补我们的生命在平地上的所有亏空。
野花的目光是慈悲的、宁静的,心胸也必然是宽容的、明亮的。
野花肯定能记住我们的脸,只是,我们连野花的名字都没有弄清楚,
就要仓促地脱离它们的关怀,重回凡尘度日,带着低矮的欲望与蹉跎。
沙棘果熟了。这是四姑娘山一带随处可见的野果,它的味道就是川西高原的味道,有一种高深莫测的酸,有一种难以捉摸的甜,还有一种鬼迷心窍的涩。
神秘的湖水,倒映着神秘的高原蓝。
树枝死而不朽,僵硬的手指直插云霄。
这里是人参果坪,双桥沟最迷人的景点之一。据说,每到夏天,野花就会在这里铺开花毯,溪水中流动的全都是花的影子。
秋色缠绵,层林尽染。我们从天而降,接受野花的引领。
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
我在桥上看雪山,雪在雪山上看我。
离开四姑娘山,我和老伴在途中(巴郎山垭口)留影。
2016-03-29发布拍摄于2018-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