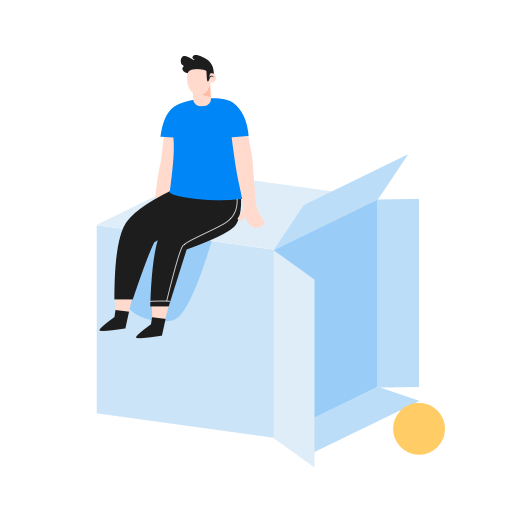格尔木
登山,是谁的精神鸦片(玉珠行记)
——登山,是谁的精神鸦片
C1的雪在地上疯狂流淌,不一会儿就淹没了帐篷的入口。
次旺抱着膝盖,呆呆的看着炉头。我冷,他说。
小风烧着水,帐篷里还弥漫着刚才火锅的味道,却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他沉默了几秒后说,我也冷。
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总以为他们是不一样的,以为他们是超越普通人的存在,他们现在却说冷,象孩子一样怀念拉萨的藏面。我蜷缩在睡袋里默默难受,却无能无力。好象这一路跟着小风的步伐,看着他的包越来越沉,身子越来越躬,而我却无力分担。
刚到C1的时候,小风调侃的问我晚上想跟谁睡,我暗自尴尬恼怒,没有给答案。铺睡垫的时候,却毫不犹豫把自己的铺在他和次旺中间,我知道这样会比较暖和,更不用像大本营那两晚那样辗转反侧担心自己被风带走。
呼吸凝结在内帐上,结成一颗亮晶晶的心,惊喜的横竖左右拍着。
帐篷里每一个空间信号强弱不一,我们跪在地上举着手机无比虔诚的寻找信号,互相打着头灯拍照,发几张图片,然后显摆自己又得到了几个赞。
又或是装得嗲嗲的,在手台里对某位只见过两面的协作说我想他了,再装作害羞不敢多说,任由小风和次旺捏细了嗓子自由发挥。
你们知道,我一直喜欢这样傻乎乎的开心。你们觉得的苦,我从来不觉得。
小风曾问我为什么要登山,我随口回答:开心啊。下山后,闺蜜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给不出正确答案。我这一看似弱质的女子,真的不想去挑战或证明什么,但我知道,当我站在山巅,会很快乐。行走,这些年对我来说,是戒不了的精神鸦片。
旦增曾与我聊起贪嗔痴,我说我不想戒,我若不痴又如何会来登山,我的欲望已经很少很少,若这点痴也要放下,岂不成尼姑了。那你登不上的话,会痛苦吗?会。既然会痛苦,为什么还要痴?不对,我会遗憾,会难受,但也许,那不是痛苦,不会折磨我。
可我从没想过,我会真的登不上玉珠这样一座被我视为过渡的雪山。
昨天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又回到玉珠,也许是从未离开,我在山脚下等了很久。
山上有只会吃人的兔子,我不敢一个人上去。
山下有很多专业的登山队,我想随便找支队伍跟着,他们在精密的仪器上比划半天,神情严肃的说,天气不好,我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登顶。
我干嚎着,流不出眼泪。
我一直都明白,世界是个疯人院。
——靠谱的马卡鲁,土豪队友,和求赞助的我
回来后,我一直不遗余力的向朋友推荐马卡鲁户外,确实因为他们是我遇见的最好的户外俱乐部,没有之一。
(photo by 小风)
旦增,我们戏称他是马卡鲁形象代言人。因为知道玉珠绝不是我最后一座雪山,所以曾8次登顶珠峰的旦增是我选择马卡鲁唯一的原因。非常喜欢旦增录制的《极致玩家》,当我们的爱好变成他们的工作,所有煽情的理由都如此苍白而又矫情。历经太多生死,旦增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正如一位队友所说的,我们在选择登山俱乐部的同时,更是在选择把命交给谁。听旦增说各种登山轶事是我们最大的消遣,把某位登山美女的故事说了好几遍之后,校长说,聊聊小风吧。
小风,拉漂,马卡鲁市场推广,高山摄影师、高山厨师、高山烧洗脚水工......小风在微信上酷的,有问必答,却惜字如金。见了面才知道,这孩子是内向,我们胡侃的时候,他大部分时候只是灿烂的笑笑。熟悉了才发现,这厮贫得很,一不小心就会中他圈套,没事还老爱拿次旺打趣。小风是强驴,这一路跟着他的节奏很舒服,重装的他应是压着步子在等我。小风,格拉丹东时,改名无风可好~
次旺跟小风学了一口东北味儿的普通话,配上那张藏族汉子的脸,却是有些滑稽。拍照时,他总是抿着嘴腼腆的笑,手机里却尽是一些超级自恋的自拍照,抱着吉它弹唱的次旺,自信得让我差点没认出来。小风戏说次旺想到上海看美女。次旺呀,那些水泥森林里生长的玫瑰,美则美矣,又哪里比得高原的格桑花有血有肉。不过,我定会陪你在上海最繁华的街头把美女看个够,直到把她们都看成红粉骷髅,回去你便随旦增皈依了吧。
(从左至右依次是:小风、我、仙乐飘飘、旦增、校长、次旺、淡定哥)
队员一共四人,除了我都是土豪,他们提及慕士塔格、卓奥友,甚至珠峰的时候,都说自己要好好锻炼身体,让我努力拉赞助,好象我缺的只是钱似的。我以前曾不止一次的口出狂言,钱就是个屁。忽然爱上登山这项运动,我发现,没钱我就是个屁。队友们一直打趣着提建议,红裙、旗袍、潜水服......要拍出什么样的登山造型,才能拉到赞助。旦增说,你来我这里当协作吧。我愣了。他又说,到底是想登山呢,还是想拉赞助呢?众人笑道,怎么忽然笨了,还不赶紧应下。
校长不是校长,他网名叫尼玛次仁(与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同名)。校长不喜欢徒步,只爱登山,这前所未有的挑战带给他重生的鲜活感,想必这也是登山多土豪的原因。校长登过技术级的雀儿山,这次只是陪夫人来登座六千级的雪山,作为慕仕塔格的敲门砖。
飘飘姐,大家对她她的称呼比较混乱,时而嫂子,时而姐。飘飘姐以前是运动员,虽然没有太多高海拔登山经验,平时也不怎么锻炼,根基到底还是好,爬起来山来毫不含糊。每每姐称校长是家长时,我会暗自感慨,做女人便该如此,事业有成,却依然小鸟依人。
淡定哥在出发前一天开始买装备,当天早上理行李,没赶上飞机,再改签。旦增检查装备时,他似乎什么也没带…...幸而马卡鲁什么装备都多带了一套。大本营时,淡定哥终于不再嫌弃旦增那件似乎从来没洗过的羽绒服,裹着宽宽大大的衣服,戴着歪歪扭扭的帽子,高反得病病殃殃,看着好生可怜。哥,好好锻炼,来年再战。
每每被称作强驴时,我嘴上谦虚,心中窃喜。队友们不耻下问时,我作无辜状得瑟:我体能其实真的一般,就是天生高原体质呀~马卡鲁的伙伴们笑而不语,他们见过太多的女汉子,象我这样的又算得了是什么。
——玉珠峰不是珠峰,也没有人会偷灯
玉珠峰,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
出发前,朋友圈里以为我去登珠峰的大概可以凑成两桌麻将。其中大部分是同事或同学。
命运很奇怪,这些明明距离最近的人,却相隔最远,但这不并影响我和他们的愉快相处。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着寻找着平衡。
格尔木到玉珠,一路都是戈壁,漫天都是尘土。大本营的天空与大地连成一片灰色。尽管如此,晚上也还是会有星星。
(忽然发现刚才在老妈家忘记把玉珠星空的照片传8264相册了,论坛竟然不支持mac上传照片,此处空照片一片。。。)
远处的野驴会偷看我们方便,胆小的地鼠会趁无人之时出来觅食。
(photo by 小风)
(photo by 次旺)
再如何严重的脸盲症,我还是第一眼认出了玉珠。
传说中的馒头山,近看坡度也不似想象中那么缓,协作们远远的指着山脊,说上山的路该如此这般,我胡乱点着头。前世我定是向导,把这辈子的方向感全都透支了。
旦增说有一次,一队自驾青藏的旅人,看到玉珠,兴奋得拐进了大本营,问他们这里是不是珠峰。瞬间觉得自己并不是最路痴的,朋友圈的小白们也不算太白。
大本营有一排矮矮的砖房,却空关着无人问津。各俱乐部的帐篷四处散落在碎石上,马卡鲁带了厚厚的棉褥子,睡得却是一点也不硌人。
营地的风很大,初到那天的下午,亲眼看到某俱乐部的两顶帐篷被风吹走,旦增拼命追赶,也没风的速度快。
小风和次旺搬了很多大石头压着帐篷,再用风绳把四顶帐篷连在了一起。即使如此,晚上听到肆虐的风声,迷迷糊糊的总觉得自己是只纸鹞子,在空中飘飘荡荡的,也许会随时跌落。
(photo by 小风)
(by 小风)
我生长的城市没有雪,它们在低空就会化成雨,或是脏脏湿湿的让人没有触碰的欲望。我只能走很远的路去看雪,或很北,或很高。
我在雪地上最经典最没创意的造型便是抛着雪笑靥如花。我最喜欢老崔的一首歌是《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喜欢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妈妈每次看到我从远方拍回的照片,总是奇怪,不就是漫天的雪吗,你就这样喜欢?是啊,我笑着无法解释。感谢我的妈妈,我从不指望摩羯的母亲能理解双鱼的我,幸而她一直纵容我。
(by 小风)
雪地上的行走总是让我很兴奋,冰雪坡练习我第一个撒开了蹄,刚走没几步,旦增和小风便扯着嗓子批评我走得太快,没节奏。闷闷的有点委屈,人家分明一点也不累。于是只能跟着旦增一步一个脚印的开始太空漫步。
冰坡的练习,原本只是体验,没想到冲顶那天却是派上了大用处,大面积的亮冰是众人始料未及的。
回程时,与小风充军似的速度冲回了营地。这厮耍酷,也不管我跟不跟得上,全程没有看我一眼。第一次穿高山靴的我,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努力着没摔跤,咬着牙保持距离。
接近营地的时候,遇到青登协的盘问,问我们是不是偷灯的。小风说我们是旦增的人,便挥手让我们走了。
你不是说大本营没偷东西的人?我实在忍不住好奇问了这个闷葫芦一句。
恩。回答得很果断。
回到吃饭的圆帐,次旺已经贴心的炖好了冰糖雪梨。我吃着甜羹,看着帐篷上的灯泡,依然还是不死心了的,指着灯泡继续问那闷葫芦:你不是说大本营没偷东西的人?为什么还有人要偷灯呢?
小风乐了,是偷登,未经许可擅自登山,不是偷灯,谁要那玩意儿啊,帐篷里哪样儿不比灯泡值钱啊。
据说那伙偷登的人是网上自行组织的,失踪两人尚未下山,其他人就已经撤退了。晚上的时候,其中一个受了伤回到大本营。我们冲顶那天,一路都是他流的血,我走路很认真,啥都没看到。
深夜的时候,旦增和青登协的一个协作旦增多吉出发去寻找失踪的另一人。未果,据说他已从另一面下了山,回到了格尔木。
(深夜,旦增出发去寻找失踪的偷登者)
关于这些山被垄断的事实,我不予置评。昂贵的登山费用把一些爱好者拒之门外,我也感同深受。但是,登山的意义何在?什么又是户外精神?越来越浮夸的户外圈,让我越来越不适应。
——下去吧,这就是登山
(大本营出发,by 次旺)
离开大本营的时候,天空飘着雪花,我们向着看不见的玉珠峰出发,每一个都信心满满。
临走前,次旺抽走了我硕大的防潮垫,挂在他的包上,说是山上风大,我背着会不安全。我悻悻的有点遗憾,想冒充一下重装都不行。
去C1的路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飘飘姐在中间找到些“回锅肉”,小风看上几块,说是可以当桌板。这些石头间寸草不生,天地混沌一片,据说含氧量很低。
(路上,by 次旺)
go pro那时候尚未罢工,镜头里尽是小风摇晃的背影,我说是他正好在我的镜头里,他说也不知道是谁,蹭蹭蹭的就追上来了。
除了喜欢休息等队友,小风重装的的节奏对我来说堪称完美,一路跟着他不紧不慢的走在所有人前面。当我啃着刚卤好不久还温热着的鸡腿,看着其他队伍的人慢慢悠悠上来,嘴里喊着加油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小得瑟的,得瑟鸡腿,也得瑟速度。
(一只鸡腿带来的满足感)
也许是走得实在太无聊了,小风这个闷葫芦居然开始打趣起我悄然流下的鼻涕和参差不齐的牙齿。我默默的擤了擤鼻涕,连同着我的牙尖嘴利一起吞回了肚子里。姐这两天还要倚仗你,我忍。
当我开始觉得肩膀有点酸的时候,C1营地到了。(抱歉,我实在是没有任何高反,爬得也不累,写不出太多矫情的感受来充字数。)次旺远远的挥着手招呼我们挑帐篷。我一头栽了进去,搓着冰冷的手脚,便不想再出去。
(雪线以上兼兄弟,C1的帐篷好象是爱尚峰的,photo by 次旺)
开始的积雪浅浅的,很快的,山上的雪便和着风一起肆虐起来。半小时后出去方便,雪已没过了脚踝。营地空荡荡的,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除了我们三个,另一支队伍也到了一个人,进进出出的忙碌,很是不便。于是我优雅的捂脸下蹲,再镇定的踱着小步回到帐篷。
(门厅处的积雪越来越厚)
(C1的晚餐居然是我最爱的火锅)
再一次出去已是晚上。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在煎熬,到底是选择憋死还是冻死。我艰难的做出选择后,深夜的营地里出现了一个如厕不捂脸,裤子穿得乱七八糟,连滚带爬仪态全无的女子。帐篷里两男人还嫌弃我一身的雪,把我堵在门口,使劲把我拍打一番,才放我进去。于是我决定,晚上再也不喝水了。
(内帐里飘进的雪,装了满满一锅)
凌晨三点,闹钟响起,我一个劲儿在睡袋里蹬着脚,假装自己已起床好几次。最后的挣扎毁于小风无情的敲打,便象只大虫子一样,裹在睡袋里,挪着身子给炉头腾地方。小风有个特点,喜欢边做饭边夸自己,连烧个麦片都要不停的问,香吧,好吃吧。
吃完很香很浓的麦片,再很费劲的把35码的脚塞进39码的La Spotiva小黄靴。然后便像人偶般被协作们伺候着穿冰爪和安全带。
我的冰爪有些问题,次旺、旦增、小风轮流帮我摆弄也没修好。所有的人都已经出发,最前面的人已经出发了近一小时。我有些急了,要知道我是想上山看日出的,唔,最好还能有云海,就象去年他们看到的那样。
(去年10月玉珠的云海,by 小风)
旦增一点也不急,说道,她没事,反正她走得快。
最终旦增把他的冰爪脱了一只给我,便大步流星去追赶校长他们去了。
5点,我和小风正式出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赶上了大部队。小风刚开始很低调地跟着队伍前进,终于还是忍受不了别人的节奏,开始超越其他人,最后和我换了个头灯,走在第一个开始找路。
我很理解那些在雪坡上二三十步一歇的人们,几年前在哈巴的绝望坡,我也和他们一样。曾几何时,六千以下的海拔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
地面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亮冰,如果风没有这么大,这么一路踢着冰坡前进,应该会挺有意思。
地上的雪和冰碴被风带起,也许还有碎石,狠狠打在脸上,我边走边举着手挡风,狼狈不堪。学不会小风说的斜着身子走路,毕竟不是属螃蟹的。
随着海拔的上升,风越来越大。走到横切的亮冰路段,我只能躬身拄着冰镐,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
小风,风大的时候,你等一下我好不好。忽然觉得小风这名字起得甚是不好。
这孩子很乖,除了等一下,偶然还会帮着挡一下风。再就是总是逼着我喝水。
我不渴,不喝。
喝。
就一个字,看在还挺爷们的份上,我总是乖乖就范,既而在心里衰衰的想,姐还有1升的水还没动过呢,怎么尽给你减负了。
冰爪又松了,摆弄了很久。另一队的节奏也很稳定,慢慢的又走到了我们前面。当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那支队伍开始有人下撤。
走到第一段路绳的时候,我们前面便没有人了。这时候,旦增通过手台告诉小风,山上除了我们两个,所有的人都已经下撤了。
我们下去吧,风太大了,很危险。
我想试试。
好吧。你带能量棒了吗?吃一点。
带了,我不饿。
我饿了,给我吃点。
那时候的风,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心悸。即使抓着上升器,我依然走几步便被风吹倒一步,于是便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轻那么瘦。
我低着头,凭着一股傻劲儿,摇摇晃晃的走完了第一段路绳。
我停下,拉着绳子,回头看着小风,好象一个想要得到老师鼓励的孩子般看着他。有些慌张,更多的是期待。
他脸已冻得通红,皱着眉头看着我。
下去吧,危险。
下去是不是就要回格尔木了?
是。
我不想下。
这么大的风,上去要失温的。
我的衣服很好,是始祖鸟顶级的登山系列,我不冷,真的一点也不冷。而且也不累,还没开始觉得累。
我知道。好吧,再陪你往上走一段吧。
第二段路绳快走完的时候,遇到那天最大的一阵风,我倒退了好几步。
我拉着路绳,好象做了错事般,回过头,有些心虚。完了,我该挺住不退的,这下他又要说危险了。
下去吧,这就是登山。
听到这句话,忽然鼻子就酸了。
妈妈说,在别的孩子还只会嚎淘大哭的两三岁,我便会看着她默默流泪,倔强的不发一点声音。
我抿着嘴,努力控制着情绪,憋了半分钟后说,好吧。
曾经有人说我最大的缺点便是不会妥协。我觉得确切说,是不愿妥协。如果我们的一生如果总是在妥协,便会老得很快,终究有一天会变成自己厌恶的模样。
这一刻,我放弃了最后的坚持与倔强,选择向大自然妥协。不知道多少人能理解,对于在乎的东西,放弃是比坚持更艰难的选择。
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反省内心,忽然意识到,比起登顶,也许更让我承受不了的是失败本身。难得认真一次,我竟然失败了。从来没想过,我怎么可能登不上玉珠,可事实就是我止步于玉珠海拔六千的山脊。
小风说要给我拍张照。我闷闷的说,拍什么拍,又没登顶,走吧。下山后,方才想起,那毕竟是我人生的最高点。你说你为什么不坚持一下呢?
小风拉着我的安全绳,一路遛着我下了坡。对冰面行走不太熟悉的我,还是险些滑了好几次。
下撤的时候是8点,明晃晃的太阳很刺眼,整片天地都在反光。那副号称次顶级的smith雪镜在天刚亮的时候就已被我弄残,便一路眯着眼睛流着泪下了山。
旦增在C1的帐篷门口等我们,看到我的时候一脸严肃,读不懂他脸上的表情,也不想说话,不管不顾一身的雪往帐篷里一坐,然后很淡定的轻声通知他们:我雪盲了。
他们非是用纱布把我的左眼包了起来,而我竟有心情自拍了发朋友圈,引来赞声一片。自然记得屏蔽了家人,省得他们担心。
再往后下到大本营的路,我睁着独眼,飘浮在那些砂石路上。遗失了左边的世界后,脑平衡严重失调,晕晕乎乎的,做梦般不真实。
回到格尔木,洗了把澡,挫败感很快便随着雪盲一起消失了。人生能有几次,会在雪线之上,在这样的狂风中拼命摇晃。而玉珠,我终有一天还会再来。
说来不怕看官们笑话,出发前,我给自己玉珠行记想好的名字是:我不是最美的花朵,但我要盛开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依然还是想用这句话收尾,送给自己,亦送给所有热爱雪山的女子。
(马卡鲁户外定制的为震区祈福的旗子,原本打算登顶展示)
qdjn 发表于 2015-11-23 21:37
随地啊。。。不会有人偷看的,大家自顾不暇的,谁有空看女人尿尿啊。。。重名重名 发表于 2015-8-17 16:21
[quote]另一种蓝 发表于 2015-5-31 13:36
——登山,是谁的精神鸦片
你好,很久没来,才看到,不知道现在回复晚不晚,玉珠虽然挺好登的,但特点就是风大,我是15年5月遇到这种天气,本来想9月下旬去弥补一下遗憾的,还好没去,据说9月底那次风更大,C1的帐篷都被掀起来了。drzhangmh 发表于 2015-8-5 08:58
因为冲顶那天smith的雪镜镜脚断了,而且一直起雾,就脱了Janedan64 发表于 2016-5-14 08:04
是旦增转的游记的那个妹子吗?羡慕你们的好运气,去年9月底也是大风,一个人没登顶,庆幸没去,此生大概与玉珠无缘了be3226 发表于 2016-5-15 00:52
你好,我的订阅号是“浮生四季”,自认为是做得不错的个人订阅号〜,欢迎关注
个人微信的话,你后台给我留言,我加你啊〜be3226 发表于 2016-5-15 13:55
谢谢〜会继续努力〜〜jiaoniren 发表于 2016-5-17 22:14
作为一个户外菜鸟,第一次看到女生登山的记录帖,首先为不矫情赞一个。
下撤的遗憾和之后的自我和解 ...
谢谢,后来登了格拉丹东,便没有对玉珠的执念了。
我的体会是只要天气好,没有严重高反,身体素质还可以的,都应该登得上玉珠,加油〜
——登山,是谁的精神鸦片
C1的雪在地上疯狂流淌,不一会儿就淹没了帐篷的入口。
次旺抱着膝盖,呆呆的看着炉头。我冷,他说。
小风烧着水,帐篷里还弥漫着刚才火锅的味道,却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他沉默了几秒后说,我也冷。
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总以为他们是不一样的,以为他们是超越普通人的存在,他们现在却说冷,象孩子一样怀念拉萨的藏面。我蜷缩在睡袋里默默难受,却无能无力。好象这一路跟着小风的步伐,看着他的包越来越沉,身子越来越躬,而我却无力分担。
刚到C1的时候,小风调侃的问我晚上想跟谁睡,我暗自尴尬恼怒,没有给答案。铺睡垫的时候,却毫不犹豫把自己的铺在他和次旺中间,我知道这样会比较暖和,更不用像大本营那两晚那样辗转反侧担心自己被风带走。
呼吸凝结在内帐上,结成一颗亮晶晶的心,惊喜的横竖左右拍着。
帐篷里每一个空间信号强弱不一,我们跪在地上举着手机无比虔诚的寻找信号,互相打着头灯拍照,发几张图片,然后显摆自己又得到了几个赞。
又或是装得嗲嗲的,在手台里对某位只见过两面的协作说我想他了,再装作害羞不敢多说,任由小风和次旺捏细了嗓子自由发挥。
你们知道,我一直喜欢这样傻乎乎的开心。你们觉得的苦,我从来不觉得。
小风曾问我为什么要登山,我随口回答:开心啊。下山后,闺蜜也问了我这个问题,我给不出正确答案。我这一看似弱质的女子,真的不想去挑战或证明什么,但我知道,当我站在山巅,会很快乐。行走,这些年对我来说,是戒不了的精神鸦片。
旦增曾与我聊起贪嗔痴,我说我不想戒,我若不痴又如何会来登山,我的欲望已经很少很少,若这点痴也要放下,岂不成尼姑了。那你登不上的话,会痛苦吗?会。既然会痛苦,为什么还要痴?不对,我会遗憾,会难受,但也许,那不是痛苦,不会折磨我。
可我从没想过,我会真的登不上玉珠这样一座被我视为过渡的雪山。
昨天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我又回到玉珠,也许是从未离开,我在山脚下等了很久。
山上有只会吃人的兔子,我不敢一个人上去。
山下有很多专业的登山队,我想随便找支队伍跟着,他们在精密的仪器上比划半天,神情严肃的说,天气不好,我们计划用一年的时间登顶。
我干嚎着,流不出眼泪。
我一直都明白,世界是个疯人院。
——靠谱的马卡鲁,土豪队友,和求赞助的我
回来后,我一直不遗余力的向朋友推荐马卡鲁户外,确实因为他们是我遇见的最好的户外俱乐部,没有之一。
(photo by 小风)
旦增,我们戏称他是马卡鲁形象代言人。因为知道玉珠绝不是我最后一座雪山,所以曾8次登顶珠峰的旦增是我选择马卡鲁唯一的原因。非常喜欢旦增录制的《极致玩家》,当我们的爱好变成他们的工作,所有煽情的理由都如此苍白而又矫情。历经太多生死,旦增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正如一位队友所说的,我们在选择登山俱乐部的同时,更是在选择把命交给谁。听旦增说各种登山轶事是我们最大的消遣,把某位登山美女的故事说了好几遍之后,校长说,聊聊小风吧。
小风,拉漂,马卡鲁市场推广,高山摄影师、高山厨师、高山烧洗脚水工......小风在微信上酷的,有问必答,却惜字如金。见了面才知道,这孩子是内向,我们胡侃的时候,他大部分时候只是灿烂的笑笑。熟悉了才发现,这厮贫得很,一不小心就会中他圈套,没事还老爱拿次旺打趣。小风是强驴,这一路跟着他的节奏很舒服,重装的他应是压着步子在等我。小风,格拉丹东时,改名无风可好~
次旺跟小风学了一口东北味儿的普通话,配上那张藏族汉子的脸,却是有些滑稽。拍照时,他总是抿着嘴腼腆的笑,手机里却尽是一些超级自恋的自拍照,抱着吉它弹唱的次旺,自信得让我差点没认出来。小风戏说次旺想到上海看美女。次旺呀,那些水泥森林里生长的玫瑰,美则美矣,又哪里比得高原的格桑花有血有肉。不过,我定会陪你在上海最繁华的街头把美女看个够,直到把她们都看成红粉骷髅,回去你便随旦增皈依了吧。
(从左至右依次是:小风、我、仙乐飘飘、旦增、校长、次旺、淡定哥)
队员一共四人,除了我都是土豪,他们提及慕士塔格、卓奥友,甚至珠峰的时候,都说自己要好好锻炼身体,让我努力拉赞助,好象我缺的只是钱似的。我以前曾不止一次的口出狂言,钱就是个屁。忽然爱上登山这项运动,我发现,没钱我就是个屁。队友们一直打趣着提建议,红裙、旗袍、潜水服......要拍出什么样的登山造型,才能拉到赞助。旦增说,你来我这里当协作吧。我愣了。他又说,到底是想登山呢,还是想拉赞助呢?众人笑道,怎么忽然笨了,还不赶紧应下。
校长不是校长,他网名叫尼玛次仁(与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同名)。校长不喜欢徒步,只爱登山,这前所未有的挑战带给他重生的鲜活感,想必这也是登山多土豪的原因。校长登过技术级的雀儿山,这次只是陪夫人来登座六千级的雪山,作为慕仕塔格的敲门砖。
飘飘姐,大家对她她的称呼比较混乱,时而嫂子,时而姐。飘飘姐以前是运动员,虽然没有太多高海拔登山经验,平时也不怎么锻炼,根基到底还是好,爬起来山来毫不含糊。每每姐称校长是家长时,我会暗自感慨,做女人便该如此,事业有成,却依然小鸟依人。
淡定哥在出发前一天开始买装备,当天早上理行李,没赶上飞机,再改签。旦增检查装备时,他似乎什么也没带…...幸而马卡鲁什么装备都多带了一套。大本营时,淡定哥终于不再嫌弃旦增那件似乎从来没洗过的羽绒服,裹着宽宽大大的衣服,戴着歪歪扭扭的帽子,高反得病病殃殃,看着好生可怜。哥,好好锻炼,来年再战。
每每被称作强驴时,我嘴上谦虚,心中窃喜。队友们不耻下问时,我作无辜状得瑟:我体能其实真的一般,就是天生高原体质呀~马卡鲁的伙伴们笑而不语,他们见过太多的女汉子,象我这样的又算得了是什么。
——玉珠峰不是珠峰,也没有人会偷灯
玉珠峰,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
出发前,朋友圈里以为我去登珠峰的大概可以凑成两桌麻将。其中大部分是同事或同学。
命运很奇怪,这些明明距离最近的人,却相隔最远,但这不并影响我和他们的愉快相处。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理想与现实间,摇摆着寻找着平衡。
格尔木到玉珠,一路都是戈壁,漫天都是尘土。大本营的天空与大地连成一片灰色。尽管如此,晚上也还是会有星星。
(忽然发现刚才在老妈家忘记把玉珠星空的照片传8264相册了,论坛竟然不支持mac上传照片,此处空照片一片。。。)
远处的野驴会偷看我们方便,胆小的地鼠会趁无人之时出来觅食。
(photo by 小风)
(photo by 次旺)
再如何严重的脸盲症,我还是第一眼认出了玉珠。
传说中的馒头山,近看坡度也不似想象中那么缓,协作们远远的指着山脊,说上山的路该如此这般,我胡乱点着头。前世我定是向导,把这辈子的方向感全都透支了。
旦增说有一次,一队自驾青藏的旅人,看到玉珠,兴奋得拐进了大本营,问他们这里是不是珠峰。瞬间觉得自己并不是最路痴的,朋友圈的小白们也不算太白。
大本营有一排矮矮的砖房,却空关着无人问津。各俱乐部的帐篷四处散落在碎石上,马卡鲁带了厚厚的棉褥子,睡得却是一点也不硌人。
营地的风很大,初到那天的下午,亲眼看到某俱乐部的两顶帐篷被风吹走,旦增拼命追赶,也没风的速度快。
小风和次旺搬了很多大石头压着帐篷,再用风绳把四顶帐篷连在了一起。即使如此,晚上听到肆虐的风声,迷迷糊糊的总觉得自己是只纸鹞子,在空中飘飘荡荡的,也许会随时跌落。
(photo by 小风)
(by 小风)
我生长的城市没有雪,它们在低空就会化成雨,或是脏脏湿湿的让人没有触碰的欲望。我只能走很远的路去看雪,或很北,或很高。
我在雪地上最经典最没创意的造型便是抛着雪笑靥如花。我最喜欢老崔的一首歌是《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喜欢那句“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妈妈每次看到我从远方拍回的照片,总是奇怪,不就是漫天的雪吗,你就这样喜欢?是啊,我笑着无法解释。感谢我的妈妈,我从不指望摩羯的母亲能理解双鱼的我,幸而她一直纵容我。
(by 小风)
雪地上的行走总是让我很兴奋,冰雪坡练习我第一个撒开了蹄,刚走没几步,旦增和小风便扯着嗓子批评我走得太快,没节奏。闷闷的有点委屈,人家分明一点也不累。于是只能跟着旦增一步一个脚印的开始太空漫步。
冰坡的练习,原本只是体验,没想到冲顶那天却是派上了大用处,大面积的亮冰是众人始料未及的。
回程时,与小风充军似的速度冲回了营地。这厮耍酷,也不管我跟不跟得上,全程没有看我一眼。第一次穿高山靴的我,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努力着没摔跤,咬着牙保持距离。
接近营地的时候,遇到青登协的盘问,问我们是不是偷灯的。小风说我们是旦增的人,便挥手让我们走了。
你不是说大本营没偷东西的人?我实在忍不住好奇问了这个闷葫芦一句。
恩。回答得很果断。
回到吃饭的圆帐,次旺已经贴心的炖好了冰糖雪梨。我吃着甜羹,看着帐篷上的灯泡,依然还是不死心了的,指着灯泡继续问那闷葫芦:你不是说大本营没偷东西的人?为什么还有人要偷灯呢?
小风乐了,是偷登,未经许可擅自登山,不是偷灯,谁要那玩意儿啊,帐篷里哪样儿不比灯泡值钱啊。
据说那伙偷登的人是网上自行组织的,失踪两人尚未下山,其他人就已经撤退了。晚上的时候,其中一个受了伤回到大本营。我们冲顶那天,一路都是他流的血,我走路很认真,啥都没看到。
深夜的时候,旦增和青登协的一个协作旦增多吉出发去寻找失踪的另一人。未果,据说他已从另一面下了山,回到了格尔木。
(深夜,旦增出发去寻找失踪的偷登者)
关于这些山被垄断的事实,我不予置评。昂贵的登山费用把一些爱好者拒之门外,我也感同深受。但是,登山的意义何在?什么又是户外精神?越来越浮夸的户外圈,让我越来越不适应。
——下去吧,这就是登山
(大本营出发,by 次旺)
离开大本营的时候,天空飘着雪花,我们向着看不见的玉珠峰出发,每一个都信心满满。
临走前,次旺抽走了我硕大的防潮垫,挂在他的包上,说是山上风大,我背着会不安全。我悻悻的有点遗憾,想冒充一下重装都不行。
去C1的路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飘飘姐在中间找到些“回锅肉”,小风看上几块,说是可以当桌板。这些石头间寸草不生,天地混沌一片,据说含氧量很低。
(路上,by 次旺)
go pro那时候尚未罢工,镜头里尽是小风摇晃的背影,我说是他正好在我的镜头里,他说也不知道是谁,蹭蹭蹭的就追上来了。
除了喜欢休息等队友,小风重装的的节奏对我来说堪称完美,一路跟着他不紧不慢的走在所有人前面。当我啃着刚卤好不久还温热着的鸡腿,看着其他队伍的人慢慢悠悠上来,嘴里喊着加油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小得瑟的,得瑟鸡腿,也得瑟速度。
(一只鸡腿带来的满足感)
也许是走得实在太无聊了,小风这个闷葫芦居然开始打趣起我悄然流下的鼻涕和参差不齐的牙齿。我默默的擤了擤鼻涕,连同着我的牙尖嘴利一起吞回了肚子里。姐这两天还要倚仗你,我忍。
当我开始觉得肩膀有点酸的时候,C1营地到了。(抱歉,我实在是没有任何高反,爬得也不累,写不出太多矫情的感受来充字数。)次旺远远的挥着手招呼我们挑帐篷。我一头栽了进去,搓着冰冷的手脚,便不想再出去。
(雪线以上兼兄弟,C1的帐篷好象是爱尚峰的,photo by 次旺)
开始的积雪浅浅的,很快的,山上的雪便和着风一起肆虐起来。半小时后出去方便,雪已没过了脚踝。营地空荡荡的,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除了我们三个,另一支队伍也到了一个人,进进出出的忙碌,很是不便。于是我优雅的捂脸下蹲,再镇定的踱着小步回到帐篷。
(门厅处的积雪越来越厚)
(C1的晚餐居然是我最爱的火锅)
再一次出去已是晚上。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在煎熬,到底是选择憋死还是冻死。我艰难的做出选择后,深夜的营地里出现了一个如厕不捂脸,裤子穿得乱七八糟,连滚带爬仪态全无的女子。帐篷里两男人还嫌弃我一身的雪,把我堵在门口,使劲把我拍打一番,才放我进去。于是我决定,晚上再也不喝水了。
(内帐里飘进的雪,装了满满一锅)
凌晨三点,闹钟响起,我一个劲儿在睡袋里蹬着脚,假装自己已起床好几次。最后的挣扎毁于小风无情的敲打,便象只大虫子一样,裹在睡袋里,挪着身子给炉头腾地方。小风有个特点,喜欢边做饭边夸自己,连烧个麦片都要不停的问,香吧,好吃吧。
吃完很香很浓的麦片,再很费劲的把35码的脚塞进39码的La Spotiva小黄靴。然后便像人偶般被协作们伺候着穿冰爪和安全带。
我的冰爪有些问题,次旺、旦增、小风轮流帮我摆弄也没修好。所有的人都已经出发,最前面的人已经出发了近一小时。我有些急了,要知道我是想上山看日出的,唔,最好还能有云海,就象去年他们看到的那样。
(去年10月玉珠的云海,by 小风)
旦增一点也不急,说道,她没事,反正她走得快。
最终旦增把他的冰爪脱了一只给我,便大步流星去追赶校长他们去了。
5点,我和小风正式出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赶上了大部队。小风刚开始很低调地跟着队伍前进,终于还是忍受不了别人的节奏,开始超越其他人,最后和我换了个头灯,走在第一个开始找路。
我很理解那些在雪坡上二三十步一歇的人们,几年前在哈巴的绝望坡,我也和他们一样。曾几何时,六千以下的海拔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
地面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亮冰,如果风没有这么大,这么一路踢着冰坡前进,应该会挺有意思。
地上的雪和冰碴被风带起,也许还有碎石,狠狠打在脸上,我边走边举着手挡风,狼狈不堪。学不会小风说的斜着身子走路,毕竟不是属螃蟹的。
随着海拔的上升,风越来越大。走到横切的亮冰路段,我只能躬身拄着冰镐,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
小风,风大的时候,你等一下我好不好。忽然觉得小风这名字起得甚是不好。
这孩子很乖,除了等一下,偶然还会帮着挡一下风。再就是总是逼着我喝水。
我不渴,不喝。
喝。
就一个字,看在还挺爷们的份上,我总是乖乖就范,既而在心里衰衰的想,姐还有1升的水还没动过呢,怎么尽给你减负了。
冰爪又松了,摆弄了很久。另一队的节奏也很稳定,慢慢的又走到了我们前面。当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那支队伍开始有人下撤。
走到第一段路绳的时候,我们前面便没有人了。这时候,旦增通过手台告诉小风,山上除了我们两个,所有的人都已经下撤了。
我们下去吧,风太大了,很危险。
我想试试。
好吧。你带能量棒了吗?吃一点。
带了,我不饿。
我饿了,给我吃点。
那时候的风,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心悸。即使抓着上升器,我依然走几步便被风吹倒一步,于是便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轻那么瘦。
我低着头,凭着一股傻劲儿,摇摇晃晃的走完了第一段路绳。
我停下,拉着绳子,回头看着小风,好象一个想要得到老师鼓励的孩子般看着他。有些慌张,更多的是期待。
他脸已冻得通红,皱着眉头看着我。
下去吧,危险。
下去是不是就要回格尔木了?
是。
我不想下。
这么大的风,上去要失温的。
我的衣服很好,是始祖鸟顶级的登山系列,我不冷,真的一点也不冷。而且也不累,还没开始觉得累。
我知道。好吧,再陪你往上走一段吧。
第二段路绳快走完的时候,遇到那天最大的一阵风,我倒退了好几步。
我拉着路绳,好象做了错事般,回过头,有些心虚。完了,我该挺住不退的,这下他又要说危险了。
下去吧,这就是登山。
听到这句话,忽然鼻子就酸了。
妈妈说,在别的孩子还只会嚎淘大哭的两三岁,我便会看着她默默流泪,倔强的不发一点声音。
我抿着嘴,努力控制着情绪,憋了半分钟后说,好吧。
曾经有人说我最大的缺点便是不会妥协。我觉得确切说,是不愿妥协。如果我们的一生如果总是在妥协,便会老得很快,终究有一天会变成自己厌恶的模样。
这一刻,我放弃了最后的坚持与倔强,选择向大自然妥协。不知道多少人能理解,对于在乎的东西,放弃是比坚持更艰难的选择。
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反省内心,忽然意识到,比起登顶,也许更让我承受不了的是失败本身。难得认真一次,我竟然失败了。从来没想过,我怎么可能登不上玉珠,可事实就是我止步于玉珠海拔六千的山脊。
小风说要给我拍张照。我闷闷的说,拍什么拍,又没登顶,走吧。下山后,方才想起,那毕竟是我人生的最高点。你说你为什么不坚持一下呢?
小风拉着我的安全绳,一路遛着我下了坡。对冰面行走不太熟悉的我,还是险些滑了好几次。
下撤的时候是8点,明晃晃的太阳很刺眼,整片天地都在反光。那副号称次顶级的smith雪镜在天刚亮的时候就已被我弄残,便一路眯着眼睛流着泪下了山。
旦增在C1的帐篷门口等我们,看到我的时候一脸严肃,读不懂他脸上的表情,也不想说话,不管不顾一身的雪往帐篷里一坐,然后很淡定的轻声通知他们:我雪盲了。
他们非是用纱布把我的左眼包了起来,而我竟有心情自拍了发朋友圈,引来赞声一片。自然记得屏蔽了家人,省得他们担心。
再往后下到大本营的路,我睁着独眼,飘浮在那些砂石路上。遗失了左边的世界后,脑平衡严重失调,晕晕乎乎的,做梦般不真实。
回到格尔木,洗了把澡,挫败感很快便随着雪盲一起消失了。人生能有几次,会在雪线之上,在这样的狂风中拼命摇晃。而玉珠,我终有一天还会再来。
说来不怕看官们笑话,出发前,我给自己玉珠行记想好的名字是:我不是最美的花朵,但我要盛开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依然还是想用这句话收尾,送给自己,亦送给所有热爱雪山的女子。
(马卡鲁户外定制的为震区祈福的旗子,原本打算登顶展示)
qdjn 发表于 2015-11-23 21:37
随地啊。。。不会有人偷看的,大家自顾不暇的,谁有空看女人尿尿啊。。。重名重名 发表于 2015-8-17 16:21
[quote]另一种蓝 发表于 2015-5-31 13:36
——登山,是谁的精神鸦片
你好,很久没来,才看到,不知道现在回复晚不晚,玉珠虽然挺好登的,但特点就是风大,我是15年5月遇到这种天气,本来想9月下旬去弥补一下遗憾的,还好没去,据说9月底那次风更大,C1的帐篷都被掀起来了。drzhangmh 发表于 2015-8-5 08:58
因为冲顶那天smith的雪镜镜脚断了,而且一直起雾,就脱了Janedan64 发表于 2016-5-14 08:04
是旦增转的游记的那个妹子吗?羡慕你们的好运气,去年9月底也是大风,一个人没登顶,庆幸没去,此生大概与玉珠无缘了be3226 发表于 2016-5-15 00:52
你好,我的订阅号是“浮生四季”,自认为是做得不错的个人订阅号〜,欢迎关注
个人微信的话,你后台给我留言,我加你啊〜be3226 发表于 2016-5-15 13:55
谢谢〜会继续努力〜〜jiaoniren 发表于 2016-5-17 22:14
作为一个户外菜鸟,第一次看到女生登山的记录帖,首先为不矫情赞一个。
下撤的遗憾和之后的自我和解 ...
谢谢,后来登了格拉丹东,便没有对玉珠的执念了。
我的体会是只要天气好,没有严重高反,身体素质还可以的,都应该登得上玉珠,加油〜
2016-03-22发布拍摄于2018-01-31